作者:R·A·萨瓦尔多
翻译:LexDivina
| 上一篇 | 目录 | 下一篇 |
年轻人的深色双眼不停转动,目光从一侧扫向另一侧,始终保持着警觉。在左侧两幢由木材和粘土搭建的摇摇欲坠的小屋之间,他察觉到一丝异响。
不过是个明智地躲在阴影里玩耍的孩子罢了。
他将视线转回右边,看见一名女子深藏在窗户后面的凹穴里——所谓窗户,仅仅是墙上的一个洞而已,因为住在卡林港这个区域的居民没人能买得起玻璃。女人和窗口保持着一段距离,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注视着他,全然不知他也在观察着她。
他感觉就像是在原野上狩猎的山猫,而她只是诸多野鹿中的一只,祈祷着自己没有被他盯上。
年轻的阿提密斯·恩崔立喜欢这种感觉,这种力量。从他还是个只有九岁的男孩开始,阿提密斯[1]已经在这条街道上拼搏了五年之久——如果它也能被成为街道的话。这里只有一堆不起眼的棚屋,杂乱无章地点缀在布满车辙的泥泞空地上。
他停下脚步,缓缓转向窗口,那个女人在感受到第一丝威胁的时候就缩了回去。
恩崔立微笑起来,继续巡视着街道。这是属于他的街道,他如此告诉自己,这是他在来到卡林港之后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开辟的区域。这里本没有正式名称,但现在,因为他的存在,它得到了一个特别的标示。它是阿提密斯·恩崔立称王的地盘。
五年来他跋涉了遥远的路途,从曼农一路搭车不远千里来到此地。“不远千里”这个说法令阿提密斯不禁发笑。实际上,曼农是距离卡林港最近的城市,然而在卡林杉贫瘠的沙漠之中,即使是前往最近的城市也需要经过漫长而艰苦的旅程。
路途诚然艰苦,但恩崔立却坚持了下来。他熬过了车队的商人们残酷的役使,忍下了一个老色鬼纠缠不休的骚扰,得以存活至今。那个蓬头垢面、散发着恶臭的蠢货似乎觉得一名九岁的男孩——
阿提密斯摇了摇头,将这段记忆从脑海中驱逐开来,不愿顺着那个不可避免的思绪继续回想下去。他在车队的长途跋涉中得以幸存,而且在抵达卡林港的第二天就偷偷从商人的手里逃了出来——此前他刚刚得知他们一路带着他只是为了最后把他买作奴隶。
在那之前的回忆都毫无价值——少年如此告诉自己——无论是从曼农前来此地的旅途,还是迫使他逃离家乡踏上这条道路的可怕经历。然而他依然嗅到那个老色鬼的气息,一如他的亲生父亲和叔叔的气息。
痛苦将他逼向愤怒的边缘,令他的深色的眼眸目光冷冽,令他手臂上的久经磨练的肌肉节节绷紧。他成功了。这才是关键。这里是他的街道,安全的所在,没有人能威胁到他。
阿提密斯继续审视着他的王国,双眸左右逡巡。他捕捉到每一丝响动,注意到每一片阴影——他总是像一只捕食的山猫,寻找着猎物,而非提防危险。
“王国”的盛景令他禁不住发出了自嘲的轻笑。属于他的街道?不过是因为其他小贼不屑占有它罢了。阿提密斯要花六天的时间搜刮每一个醉倒在这片贫民区的污泥中的酒鬼,得来的钱财才勉强够他在第七天吃上一顿体面的正餐。
然而这对一名背井离乡的流浪儿而言已经足够了;在过去的五年间,他不仅藉此为生,还重拾了他的尊严。如今他已经长成了一个青年,十四岁——或者差不多快要十四岁了。阿提密斯记不清自己的确切生日,他只记得在转瞬即逝的雨季到来之前的那段短暂时光。那时家里的情况还没有那么糟糕。
年轻人再次摇了摇头,挥去这些多余的记忆。就是十四岁,他作出结论;仿佛为了加以确定一般,他低头望向自己久经日晒的柔韧身躯。他勉强有一百三十磅重,每一寸骨骼上都覆盖着紧致的肌肉。他已经十四岁了,他为此而感到自豪,因为他不仅得以存活,而且茁壮地成长了起来。他巡视着他的街道,他的王国,挺起他依然稚嫩的胸膛。甚至连老酒鬼们都畏惧他,在与他交谈时莫不展现出得体的敬意。
这是他赢来的东西,在这个小贫民窟中——千余个类似的小贫民窟,环簇着富商们饰有金边的白色大理石宅邸,就组成了名为卡林港的城市——每个人都尊敬他,畏惧他。
只除了一个人之外。
十天前有一个恶棍新来此地。这个年轻人大约比阿提密斯年长三四岁,没经过阿提密斯的同意就开始打劫倒在泥污里面的可怜虫,甚至还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住户家中,恫吓里面的居民。他迫使阿提密斯的猎物为他提供菜肴,献上他能找到的最好的贡品。
这是最令阿提密斯感到愤怒的地方。对他圈出的领地中的,阿提密斯既无怜悯之心,也并不怀有任何敬意。然而他曾经见过属于这名新来者同类的家伙——在他不堪回首的过去,在他挥之不去的噩梦之中。实际上,阿提密斯的街道完全可以容纳两名暴徒。新混混刚到的前五天,他和阿提密斯甚至都没有遇到彼此。当然,阿提密斯那些可怜的线人们谁也没有为了免受新的伤害而前来向他寻求保护。他们甚至不敢和阿提密斯说话,除非是他直接向他们发问。
尊严才是问题所在,绝不容他忽视。
阿提密斯从棚屋的拐角处窥向泥泞的小巷。“真准时。”看到新来者出现在这段相对笔直的道路尽头,他轻声说道。“不难预测。”阿提密斯勾起嘴角,心想可预测性可真是个弱点。他必须将其谨记于心。
新来的暴徒有着深色的双眼。他的头发,一如恩崔立的头发,好似坎达德绿洲之中的湖水一般漆黑,仿佛所有其他色彩都溶进了它深不可测的色调之中。阿提密斯认为他、这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卡林杉人,和他自己并没有什么不同。
是怎样痛苦的经历令面前的入侵者踏上了他的街道?他暗忖。这种同情实在不合时宜,阿提密斯自责道。怜悯之心会令你死于非命。
他深吸一口气,镇静下来,目光再次变得凛冽无情,冷冷地看着入侵者将一名步履蹒跚的老头推倒在地,扯开他那只破破烂烂的钱袋。明显是对钱袋贫乏的内容深感不满,年轻人从最近处棚屋参差不齐的边缘上扯下一块半腐烂的木板,揍向可怜的受害者的前额。老头哭喊哀求着,但那恶棍又一板拍上他的鼻子。他跪倒在地,满脸鲜血,嚎哭哀求。木板不断落在他身上,直到他破碎的面孔栽进泥浆,啜泣因此被堵回口中为止。
阿提密斯发现他并不在乎老头凄惨的命运。他关心的是他哀求新来者的事实。他乞求那个在阿提密斯·恩崔立的地盘上不请自来的恶棍,仿佛那个家伙才是他的主人。
恩崔立的双手探向口袋,伸了进去,摸着他费心带上唯一几样的武器:两小把黄沙,一块边缘锋锐的扁石。他发出一声叹息,既感到无可奈何,又因为即将到来的战斗而兴奋不已。他正要迈步转出拐角,却又驻足思忖着自己的感觉。他是那只狩猎的山猫,是此地的主宰,因此,他是在正当守卫着自己开辟的王国。然而阿提密斯还是感到一阵无可否认的悲哀,一种他不能理解的无奈之情。
在他的心灵深处,在一个被他的恐怖经历封闭藏匿起来的角落里,阿提密斯知道事情本不该如此。但这一认识却无法令他回避即将到来的战斗。相反,它令他易发愤怒。
随着一声野蛮的怒吼,阿提密斯绕过棚屋踏上空地,站到迎面走来的恶棍前进的道路上。
年长的男孩清下脚步,同样打量着他的对手。显而易见,他知道阿提密斯,正如阿提密斯知道他。
“你终于现身了。”新来者胸有成竹地发话。他比纤细的阿提密斯高大,但那具战士的身躯上没有一丝多余的重量。因为经历过更多艰苦的光阴,他的双肩成熟宽阔,肌肉尽管不算十分粗壮,却虬结如同坚韧的粗绳一般。
“我一直在找你。”他边说边缓缓逼近。他小心翼翼地姿态令阿提密斯意识到他其实要比表面上紧张得多。
“我从没躲藏。”阿提密斯回答,“你可以在任何时间找到我。”
“我何必那么费事?”
阿提密斯考虑着这个荒谬的问题,然后耸了耸肩膀,决定不回应这句狂妄自大的发言。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儿。”男人终于说道,语调突然变得尖锐起来——进一步证明他的神经已经紧绷到了极点。
“有意思,我以为我才是那个找到你的人。”阿提密斯答道。他很好地掩饰住了他的忧虑。也许这个恶棍出现在此地,出现在阿提密斯的街道上,有着他所未曾料到的目的。
“除了找到我之外你别无选择。”入侵者断言。
又来了——一个关于更深层目的的暗示。直到此时,阿提密斯才想到,这个男人——因为他的确是一个男人,而非街头流浪儿——本应早已不屑于占领像此地一般贫瘠的街区。就算他是初涉此道,作为成年的恶棍,他也应该加入城中诸多盗贼公会之一。那么他又是为什么前来此地呢?
而且还是孤身一人?
也许他被某个盗贼公会扫地出门了?
一时之间,阿提密斯担心自己可能陷入了麻烦。他的对手是个成年人,而且还可能是名阅历丰富的游荡者。恩崔立驱开了这个念头,知道自己的推理并不严密。年轻的新手们不会被卡林港的盗贼公会“扫地出门”;他们只会凭空消失,没人会去费事质疑他们突如其来的失踪。然而,眼前的对手又显然不是一个被迫独自出来闯荡的小孩。
“你是谁?”阿提密斯直接问道。话乍一出口他就后悔不迭,担心那个暴徒由此得知他一无所知的事实。在他的王国里,阿提密斯只有单枪匹马,身边并未建立起网络,也没有任何派的上用场的眼线。他对卡林港的真正权力构架几乎是一无所知。
暴徒露出一个微笑,花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审视着他的对手。阿提密斯身材矮小,正如公会情报所显示的一般,他在战斗中很可能以速度和精准见长。他站在那里,姿态轻松,双手插在破破烂烂的马裤的兜里,晒成褐色的纤细手臂暴露在外,上面覆盖着久经磨练的精致肌肉。来此之前,暴徒就被告知了阿提密斯并无同伙,然而这个男孩——在年长的盗贼眼中,阿提密斯的确还是个孩子——镇静自若,看来远比他的实际年龄成熟。
还有一件事令这个男人倍感困惑。
“你没有武器?”他怀疑地询问。
作为回应,阿提密斯只是再次耸了耸双肩。
“那么,好极了。”暴徒语气坚决地说道,仿佛刚刚作出了某个决定。为了强调这一点,他抬起那块依然滴淌着老头鲜血的木板,果断得将其抬过肩头。抬过肩头——阿提密斯意识到这是一个更加易于发起攻击的姿势。暴徒从约有二十尺开外的距离向他逼近。
阿提密斯知道,眼下发生的事情非常复杂,而他想要知道答案。
十尺。
阿提密斯保持着镇静平稳的姿态,但肌肉紧绷,准备迎接将要发生的事情。
那个男人现在离他只有五尺了。恩崔立的右手从口袋中急速挥出,扬起一把细腻的黄沙。
男人举高木板,将头扭向一侧。他大笑着将目光转回到男孩身上。“想用沙子迷住我的眼?”他难以置信地问道,语气中饱含讥讽,“在沙漠里打架竟想到用沙子,真是聪明绝顶!”
在卡林杉无数在暗中口口相传的街头斗殴用语中,这种说法的意思是“老掉牙的把戏”。然后阿提密斯重复了这个老掉牙的把戏,将手插回兜里再次挥出一把沙子。
暴徒大笑着闭上双眼进行防御。他很快就重新睁开了眼,只隔了转瞬即逝的一秒钟。然而对于双手同样灵活的阿提密斯而言,这一瞬间已经足够他抽回插在兜里的左手,掷出那块边缘锋利的石头。可供他利用的只有一个小破绽,在短短的一刻所暴露出来的那块一寸见方的目标。他必须做到完美无缺——但这正是阿提密斯从孩提时代就不得不采取的行事方式。他从家中逃进了沙漠,而在这个地方,即便是最微小的过失也会导致灭顶之灾。
锋利的石块从举起的木板旁边呼啸而过,正中暴徒的咽喉一侧。尖石切开了喉管,转向左方,割断了一条颈动脉后飞向空中。
“什——”暴徒刚要发话,却又猛然住了口,明显是因为自己声音中突然出现的嘶嘶声而惊愕不已。一道鲜血从他的项间喷涌而出,溅上他的面颊。他抬手按住伤口,手指紧握,企图止住血流。他依然保持了足够的镇定,始终没有放低那快作为临时武器的木板,准备好抵御阿提密斯的攻势。然而较为年轻的男孩已经将双手收回了口袋里,没有做出进一步的攻击。
他表现很好,阿提密斯承认,真心赞赏他的镇静和毫不松懈的防御。他表现得很好,但阿提密斯表现得完美无缺。你必须要做到完美无缺。
涌流的鲜血几乎止住了,但动脉和旁边的气管都已经被割断。
那恶棍发出一声咆哮,逼上前来。阿提密斯面不改色。
恶棍猛然停下了脚步,深色的双眼大大圆睁。他试图说话,却喷出了一口颜色刺眼的鲜血。他试图呼吸,却再次发出了可怜的汩汩声。鲜血迅速填满了他的胸腔,令他跪倒在地。
他过了很久才断气。卡林港是个冷酷无情的地方。你必须做到完美无缺。
“干得好。”一个声音从左边传来。
阿提密斯转过身,看见两个男人从一条狭窄的小巷中漫步踱出。他立即意识到他们也是盗贼,很可能来自某个公会。阿提密斯自信只有最老练的游荡者才能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如此靠近他。
阿提密斯回头望向脚边的尸体,无数问题在他脑中盘旋。现在他可以冷酷地断定这并非是一场偶遇。刚刚在他手中丧命的暴徒是被派来的。阿提密斯轻笑起来——嘲弄的一哼,而非放声大笑——将尘土踢到死去的男人脸上。
做不到完美无缺,你会横死于非命。做到了完美无缺,你会——正如阿提密斯很快发现的那般——被邀请加入当地的盗贼公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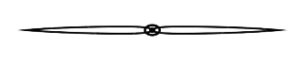
只需打个响指,想要的食物就会被立即奉上——这样的情形对阿提密斯来说几乎难以想象。他们还提供给他一张柔软的床铺,但因为担心如此奢侈的生活会令自己变得虚弱,阿提密斯依然睡在地板上过夜。
尽管如此,他们提供给他床铺的事实依然意义重大。阿提密斯并不在乎物质上的财富和愉悦,但他非常在乎这些愉悦被提供给他的事实本身。
以上是加入巴沙多尼公会的好处。实际上,作为城市中最大的盗贼公会之一,巴沙多尼公会还能提供许许多多其他的好处。然而对于一名像阿提密斯·恩崔立这样独立自主的年轻人来说,加入公会也同样有其不利之处。
公会副官西博斯·罗尤赛特,帕夏巴沙多尼为恩崔立指定的私人导师,就是诸多不利之处之一。他身上凝缩了年轻的阿提密斯·恩崔立所深恶痛绝的一切特质。好吃懒做,暴饮暴食,肥厚的眼睑永远低低压在双目上方。天生打卷的棕发之间散发着恶臭,却因为太过油腻肮脏而能够始终黏在头皮上。他衬衫的前襟总是沾着最近四顿饭的污渍残渣。除了把刚抓到的满手事物塞进那张口水四溅的嘴里,西博斯的任何动作都谈不上敏捷。但这个男人拥有精明危险的头脑。
而且还是个虐待狂。尽管他明显身手不佳,西博斯仍然是公会的七名副官之一,权力仅次于帕夏巴沙多尼本人。
阿提密斯憎恨他。西博斯曾经是一名商人,正如卡林港的许多商人那般,他和城市守卫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因此西博斯用钱财在公会中买来一个职位,得以潜入地下,逃脱卡林港令人毛骨悚然的监狱。阿提密斯知道,那笔钱财必然数目不菲,令帕夏巴沙多尼不仅接纳了这个危险的懒蛋,还将他任命为副官。
他进而敏锐地领悟到,巴沙多尼之所以选择嗜虐成性的西博斯作为阿提密斯的私人导师,是为了测试他对这个新家族的忠诚。
残忍的测试。靠在公会大厅地下的一间方形石室的方砖墙上,阿提密斯如此想到。他双臂防御性地交叉在胸前,戴着厚重手套的手指无声地敲打着手臂,很不耐烦。他发觉自己想念外面的城市中属于他的街道,缅怀他无需被任何人呼来喝去,只需跟随直觉行事的日子。只因为精准地投出了一块边缘锋锐的尖石,那些时光一去不返了。
“怎么?”西博斯再次说道,他经常像现在这样突然前来视察工作。他从扁平的宽鼻子里面抠出了一大块东西,然后,一如所有落入他婴儿般肥厚的手掌的东西那般,它迅速消失在了西博斯的嘴里。
阿提密斯没有眨眼。他的目光从西博斯转向昏暗房间的另一侧,那里有一个十加仑的玻璃箱。尽管这间石室位于地面之下足有二十尺的深度,却依然干燥而多尘。
臃肿的副官跺向玻璃箱,每一步都蹒跚不定。阿提密斯顺从地跟了上去。不过在那之前,他飞快地向站在门口的游荡者守卫点了点头。阿提密斯刚刚在街道上杀死那个暴徒的时候,就是这名游荡者前来迎接的他。他叫丹瑟,是西博斯的另一名学徒,也是阿提密斯进入公会以来交到的诸多朋友中的一个。丹瑟回应了他的暗示,悄然离开回到了大厅。
他信任我,阿提密斯暗忖,就冲这点,丹瑟可谓愚蠢透顶。
阿提密斯跟上西博斯,站到玻璃箱前方。肥胖的男人密切注视着其中纠缠成一团的橙色小蛇。
“真美啊。”西博斯说道,“多么光滑,多么精致啊。”他厚眼睑下的目光转向阿提密斯。
阿提密斯无法否认这番评论。它们是色塞利毒蛇,致命的“两步蛇”。一旦被一条色塞利毒蛇咬中,你会大叫一声,迈出两步,倒地身亡。迅速。漂亮。
即使戴着厚厚的手套,从致命的毒蛇口中挤出毒液也绝非妙事可言。不过话说回来,可恶的西博斯·罗尤赛特总是格外注意不让阿提密斯得到轻松的工作。
西博斯注视着那些撩人的毒蛇,很久之后,他回头望向右方,却发现始终一言不发的阿提密斯已经绕过了他,走向房间另一端。西博斯抑制住惊愕之情,转向年轻的游荡者,发出一声扭曲的冷笑,刻意用高高在上的笑声提醒着阿提密斯他作为一名下属的身份。
直至此时,西博斯才注意到半掩在屏风后面的四分台。一时之间,他布满斑点的粗短身形之间流露出惊讶之情,但很快就镇静了下来。“你干的好事儿?”他问道,走向屏风,示意着那张桌面上覆有玻璃的小圆桌。桌子两侧各有一根齐腰高的把手。
当西博斯经过他身边时,阿提密斯也缓缓转过头来,目光越过一侧肩膀,却并未费事回答对方的提问。既然挤蛇毒的工作由他负责,那么阿提密斯自然正是“干这好事儿”的人。除了总对他冷嘲热讽的导师,又有谁会劳神前来此地呢?
“你在公会的低层结交了不少盟友嘛。”西博斯发话;这几乎可以算是他对阿提密斯最接近赞扬的评价了。实际上,西博斯的确为此而感到动容:对一个刚刚加入公会的新手来说,能把臭名昭著的四分桌移到如此僻静便利的所在委实是一项壮举。然而当西博斯花了点时间细作思忖之后,他觉得这也没那么令人震惊。年轻的阿提密斯·恩崔立是个不容小觑的角色。这名富有魅力的年轻游荡者令许多远比他年长的恶徒也向他展现出了相当高的敬意。
诚然,西博斯深知阿提密斯·恩崔立绝非寻常扒手。他可以变成一名杰出的盗贼,跻身于此行佼佼者之列。这对巴沙多尼公会来说可能是件好事。也可能是个威胁。
阿提密斯并未转身,而是径直走过房间,在四分桌两边相对的两把椅子中的一把上坐了下来。
当然,这一挑战也不是全然出乎意料。相同的场景曾在西博斯和他残忍奴役的年轻人之间上演过好几次。更何况,年轻的阿提密斯现在必然已经知道,那个暴徒是在西博斯的授意下到棚区挑衅他的。是丹瑟告诉了恩崔立这些,西博斯猜测;等搞定了恩崔立之后,他会记得和丹瑟来场小小的谈心。肥硕的副官无声地大笑,信步穿过房间,站到已经坐下的年轻游荡者身边。他看见四只玻璃杯以相同的间隔摆放在圆桌边缘,各自盛有半杯清水。桌子中央有个空的集毒瓶。
“你要知道,我和帕夏巴沙多尼私交甚密。”西博斯说道。
“我只知道,一旦你坐到那把椅子里,你就自愿接受了挑战。”阿提密斯回答。他伸手取走了集毒器。按照这项挑战严格的规则规定,桌子上除了四个玻璃杯之外不能摆放任何其他东西。
不出阿提密斯所料,西博斯大笑着摇了摇头。阿提密斯知道他没有权利提出这样的挑战。然而,当西博斯拍了拍他的肩膀绕向桌边的时候,他觉得略微松了一口气。肥硕的副官停住脚步,刻意查看着每一只玻璃杯,仿佛发现了什么玄机。
他只是虚张声势。阿提密斯尖锐地提醒自己。色塞利蛇毒完全澄透无色,和清水并无两样。
“你用的量足吗?”西博斯镇定自若地问道。
阿提密斯没有回答,毫无动摇。和臃肿的副官一样,他知道一滴就足以致命。
“而你只向一杯里投了毒?”西博斯问道,另一句虚浮的废话。挑战的规则再明确不过。
西博斯坐在指定的位置上,显然是接受了挑战。
阿提密斯的面具上几乎出现了裂纹,他不得不咽下一声如释重负的叹息。副官本可以拒绝他,以他竟然自以为有权力向高阶公会成员发起这项挑战为由叫人把他拖出公会开肠破肚。当然,阿提密斯认为嗜虐成性的西博斯不会采取如此直接的手段。他有多么憎恨西博斯,西博斯就有多么憎恨他。过去几十天里,西博斯在其权力所容许的范围内将那份憎恨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只有一杯?”西博斯再次询问。
“有关系吗?”阿提密斯回答,觉得这样应对堪称巧妙,“无论投过毒的是一杯、两杯,还是,我们的风险始终均等。”
肥胖的副官表情阴沉了下来。“这是四分桌。”他屈尊纡贵地解释道,“四分之一。四杯中的一杯。这是规矩。桌面转起来之后,我们每人都有四分之一的几率喝到有毒的那杯。而且,根据规则,有毒的不能多于一杯,丧命的不能多于一人。”
“只有一杯有毒。”阿提密斯肯定道。
“毒液是色塞利蛇毒,而且只有色塞利蛇毒?”
阿提密斯点点头。听在像这名年轻的游荡者一般精明的挑战者耳中,西博斯的问题无异于大声宣布他并不怕色塞利蛇毒。他当然不怕。
西博斯点头回应,换上一副和对手同样严肃的神情。“你确定要这么做?”他语气沉痛地询问。
阿提密斯没错过老练的杀手话中狡诈的言外之意。西博斯正假意赐给他反悔的机会。但那只是圈套而已。阿提密斯决定陪他玩下去。他不安地环视四周,在额头上挤出一滴汗来。“也许……”他试探性地开口,仿佛在权衡利弊。
“怎样?”漫长的停顿之后,西博斯追问。
阿提密斯作势要站起来,如同真的后悔做出了这项挑战一般。西博斯大喝一声制止了他。阿提密斯那张太过秀美的稚嫩面庞上流露出了好似发自内心的惊愕之色。
“我接受你的挑战。”副官吼道,“你没得反悔。”
阿提密斯跌坐回座位上,抓住桌面边缘用力一拉。桌面沿着中轴无声地平滑转动起来,如同赌轮一般。阿提密斯握住了身边的长杆——四分桌的制动轧之一——满脸得意笑容的西博斯也同样照做。
这很快变成了一场意志力的较量。阿提密斯和西博斯的目光交汇了,而后者第一次看清了他年轻的对手所具备的潜力。此时此刻,西博斯开始欣赏残酷无情的阿提密斯·恩崔立展现出来的那份纯粹的机敏和狡诈。然而,他对此并不畏惧,而且始终保持了足够的镇静,这令他得以注意到阿提密斯双眸中微妙的变化。在他貌似漫不经心的伪装下,面前的年轻人正在暗自密切关注着旋转的玻璃杯。
阿提密斯从桌台上捕捉到一丝微亮,一道不易察觉的闪光。而后是第二道。早在西博斯可能造访的很久之前,他就在一只杯子的杯沿上留下了一个微小的刻痕。然后阿提密斯大费周章地调整了桌子和他所坐的椅子之间的相对位置。桌面每旋转一圈,杯口的小刻痕都会反射最近处壁台上火炬的光亮,映出一丝微光——只有他才能看得见。
阿提密斯默默的计算着每次闪光之间的间隔时间,估计着桌面的转速。
“你为什么要冒这么大风险?”西博斯警觉地问道,发话干扰年轻人的注意力,“才短短几十天,你就已经恨我入骨了么?”
“是漫长的几个月,”阿提密斯纠正道,“不过比那更早。我在街道上的遭遇并不是一个巧合。那是个设计好的圈套,是我和我不得不杀死的那个人之间的一场测试。而这一切都出于你的安排。”
听到阿提密斯将他的对手称为“我不得不杀死的那个人”,西博斯得以窥见了这名年轻游荡者的动机。肮脏街道上的陌生人很可能是阿提密斯·恩崔立杀死的第一个人。公会副官会心一笑。谋杀对许多怯懦者来说都显得难以接受;无论是第一次杀人的事实,还是第一次杀人的事实引领这名年轻人踏上的道路,都不是恩崔立所追求的结果。
“我必须要知道你是否有用,”西博斯说道,承认了他的阴谋。但阿提密斯已经不再听他说话了。年轻的游荡者重新将注意力转回到对旋转玻璃杯的暗中观察上。
西博斯拉起他手边的制动闸,显著减缓了桌面旋转的速度。桌台中轴经过良好的润滑——有些人甚至声称上面施有某种魔法——因此桌面无需多大冲力就能以近乎均匀的速度保持旋转。
面对出其不意的速度变化阿提密斯并未表现出气馁。他镇静自若,重新暗自计算起转速来。每次带有记号的玻璃杯闪烁时,都恰好刚刚从西博斯面前转过八分之一圈的长度。阿提密斯调整着内心的节奏,每一圈都恰好数到八。
他看见了闪光;他在心中默数,数到九的同时猝然拉起轧杆。
桌台的转动戛然而止,玻璃杯中的液体来回激荡,水滴溅上桌面和地板。
西博斯注视着面前的玻璃杯。他想要指出年轻的游荡者并未理解四分桌挑战的真正规则——双方本应该轮流使用制动闸缓慢加力,而且最后的停止应当由被挑战者作出。但胖副官决定置之不理。他知道自己被设计了,而他并不十分在意。差不多十天之前他就早已预料到了这场较量,现在他血管里流淌的解毒剂足以中和一百条色塞利蝰蛇的蛇毒。他举起杯子;阿提密斯也同样照做。两人同时深饮一口。
五秒过去了。十秒。
“很好,”西博斯发话,“看来今天我们都没撞上那不幸的四分之一。”他将肥硕的身躯从椅子里面拔出来。“当然了,你的无礼行为将被悉数上报到帕夏巴沙多尼面前。”
阿提密斯并未流露出任何表情。他甚至没有眨眼。西博斯怀疑这名年轻的游荡者掩饰了他的惊讶之情,要不然就是满心愤懑,抑或正在试图理解为什么自己能够逃过这场突如其来的劫难。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年轻人始终不变的镇静开始令胖副官焦躁不安起来。
“你的挑战完成了。”西博斯突然高声斥道,“我还活着,而这就意味着你输了。准备好为你的无礼付出沉重代价吧!”
阿提密斯不为所动。
胖副官打了个响指,决定不再和这名年轻的新晋者纠缠。他转身离开,同时思量着他可以用来好好惩罚阿提密斯的种种方式。
那些折磨将会无比美妙,因为这次,巴沙多尼将不能再阻止西博斯了。在西博斯看来,年迈令公会会长变得太过心慈手软。曾经有好几次,当他得知胖副官准备为年轻人来一场残忍的惩罚时,巴沙多尼都为了恩崔立而出面干涉,安抚西博斯的情绪。但是这次不行。这次,巴沙多尼无法插手。这次,恩崔立根本是自作自受。
回到奢华的私人房间之后,西博斯首先来到了他装得满满的食品柜面前。众所周知,色塞利蛇毒的解毒剂会造成剧烈的饥饿感,而西博斯吃起东西来从来就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他取出一块巨大的双层蛋糕,蛋糕上点缀着糖霜和甜腻的水果。
他拿起餐刀切下了一块,却又耸耸肩膀,决定把干脆把整个蛋糕全部吃掉。他双手抓起蛋糕抬到嘴边。
“哦,聪明的小家伙!”西博斯赞叹道,将蛋糕放回桌上。
“计中有计,套里藏套!你当然知道色塞利蛇毒解毒剂的副作用。你当然知道我会跑回这里,跑到我的私人橱柜面前!而你不缺时间作下手脚,不是吗,阿提密斯·恩崔立?聪明的小家伙!”
西博斯望向窗户,考虑将蛋糕扔到街上。就让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们咽下碎屑倒地横死吧!然而,这块蛋糕如此美妙。他无法丢弃它,更何况他实在是太饿、太饿了。
他转而穿过房间来到自己的私人书桌面前,小心翼翼地打开设有陷阱的上锁抽屉,从蜡封上确认此前并没有其他人开过抽屉,确认阿提密斯恩崔立并未对这些药水动过手脚。在发现一切正常之后,西博斯心满意足地打开了抽屉底部的密格,从中取出一个价值不菲的小瓶。瓶中盛有某种琥珀色的液体,一种能够中和任何毒药的魔法药水。西博斯再次望向蛋糕。阿提密斯真的如他所想的那般聪明么?这个年轻的游荡者真的理解计中计的概念么?
西博斯长叹一声,觉得阿提密斯的确很可能就是这么聪明。一瓶万能解毒剂诚然昂贵,可蛋糕看起来又何其可口!
“我得让阿提密斯·恩崔立再给我买一瓶。”已经饥饿难耐的公会副官如此思忖着,一口喝下了解毒剂。然后他兴高采烈地冲过房间,从蛋糕边缘上撕下一小片,品尝着它的味道。蛋糕果然被下过毒了。一抹难以察觉的酸味隐藏在香甜的口感之中,令经验丰富的西博斯立即意识到了这点。
公会副官知道解毒剂能破除毒素,而他并不想让那名年轻的新进者破坏了他如此美味的一顿大餐。他搓了搓两只胖乎乎的手掌,抓起蛋糕,狼吞虎咽地大嚼特嚼,每一口里面都塞下了好几块,把盛蛋糕的银盘打扫得干干净净。
当夜,西博斯一命呜呼,死状骇人。他从酣梦中惊醒,陷入五内俱焚般的极度痛楚之中。他想要大叫,但声音淹没在了他自己的鲜血里面。
当侍者在翌日清晨找发现他的时候,他满口淤血,枕套上浸染着点点棕红色的血迹,肚皮上覆满狰狞的蓝色条纹。公会中的许多人都从丹瑟那里听说了前一日中的那场挑战,由此,年轻的阿提密斯和西博斯的横死之间的联系变得不难察觉。
帕夏巴沙多尼的强大的间谍网络忙碌了十天,终于将年轻的刺客被从卡林港的街道上抓了回来。当他被两名魁梧的年长杀手粗暴地带回公会大厅时,显得无奈多于恐惧。
阿提密斯认为巴沙多尼会为他的行为而惩罚他,甚至可能会杀了他。但知道西博斯·罗尤赛特死状惨烈,这一切也就值了。
他从未去过公会大厅最顶层的房间,从未想象过在那之中会藏有怎样的财富。不可方物的美女浑身挂满熠熠生辉的珠宝首饰,游走在每一个房间之中。到处都堆满了巨大的坐垫软椅和枕头,每隔三道拱门就有一只芳香四溢、雾气腾腾的水槽设置在那里。
大厅的一整层都完全是为了纯粹的享乐而布置,以提供各种所能想象出的欢愉。然而在阿提密斯眼中,此地的危险却更甚于诱惑。他致力于精益求精,而非坐享安乐,这里是个会令人软弱松懈的地方。
因此,当他终于站到帕夏巴沙多尼面前时,阿提密斯不禁感到诧异。这是他第一次真正面对这位老人,他的小办公室是公会这一层唯一一间并非为了舒适而建的房间,其中只有几件简单的家具——一张木桌和三把平凡无奇的椅子。
帕夏本人也和房间的风格协调一致。他身材矮小,苍老却不失威严。他的目光如其姿态般直接干脆,灰白的头发一丝不乱,衣着朴素无华。
只观察了片刻,阿提密斯就意识到这是位只得尊敬、甚至是敬畏的人。看着面前的帕夏,阿提密斯不禁再次想到,一个像西博斯·罗尤赛特一般的懒虫在这里是显得多么格格不入。他立即猜到巴沙多尼必然也对西博斯恨之入骨,而单是这一猜测本身就给他带来了一线希望。
“那么,你承认你在四分仪挑战中作弊了吗?”刻意停顿了很久之后,巴沙多尼开口问道。此间他细致地打量了一番阿提密斯,至少也像阿提密斯观察他那般细致。
“难道那不是这项挑战的一部分吗?”阿提密斯迅速回答。
巴沙多尼轻笑着点了点头。
“西博斯料到了我会作弊。”阿提密斯继续说道,“他的房间里有一个万能解毒剂的空瓶。”
“你在那上面动过手脚了?”
“我没有。”阿提密斯坦言相告。
巴沙多尼用询问之色催促年轻的游荡者继续说下去。
“药水如期发挥了作用,蛋糕也只是用寻常的毒药下过毒而已。”阿提密斯承认。
“然而……”巴沙多尼说。
“然而卡林杉还没一种解药能抵御碎玻璃的效果。”
巴沙多尼摇晃着头颅。“计中计里更有计。”他说,“套中套里还藏套。”他好奇地望向这个聪明的男孩。“西博斯有能力想到这第三阶的欺骗。”他推理道。
“但他不相信我也能。”阿提密斯立即应道,“他低估了他的对手。”
“所以他死得其所。”停顿了片刻,巴沙多尼得出结论。
“他自愿接受了挑战。”阿提密斯飞快地指出,提醒年长的帕夏,根据公会的规则,任何惩罚都必将失之不公。
巴沙多尼向后靠在他的椅子里,指尖相抵。他凝视了阿提密斯很长时间。尽管年轻的刺客理由充分,然而,在清晰地目睹阿提密斯黑暗内心中的残忍和冷血无情之后,巴沙多尼还是几乎想要下令將他处死。他知道自己永远也无法真正信任阿提密斯·恩崔立,但他也同样意识到,除非被逼到走投无路,年轻的阿提密斯不太可能同他——一名长者,而且是有望成为导师的长者——反目相向。而且,巴沙多尼也知道像阿提密斯·恩崔立这样狡黠而冷酷的游荡者会成为怎样的一笔财富——特别是当现在,当剩下五名野心勃勃的公会副官[2]都在暗自希望着他能速速横死,留出位子供其取而代之的时候。
或许我终究还是会比他们五个活得都久,帕夏如此想道,微微一笑。但对阿提密斯他只是简单地说道:“我不会惩罚你。”
阿提密斯面无表情。
“你可真是个冷血的混蛋。”巴沙多尼无可奈何地笑了一声,继续说道,声音中也同样充满发自内心的无奈,“你可以退下了,恩崔立副官。”他挥了挥布满老年斑的手,仿佛所发生的一切令他口中苦涩不已。
阿提密斯刚要转身离去,却猛然停下脚步回过头来。此时他才意识到巴沙多尼是用怎样的头衔来称呼他的。
新副官身边两名魁梧的护卫也注意到了这点。其中一人露出焦躁愤懑的神色,怒视着面前的男孩。副官阿提密斯·恩崔立?他阴郁的神色似乎在发出难以置信的询问。这个男孩,身高只有他的一半,来到公会不过数月之久。他才十四岁而已!
“也许我的第一份职责就是监督你继续受训。”阿提密斯说道,冷冷地直视着那个魁梧男人的脸,“你必须学会更好地掩饰自己的感情。”
当他同样望进那双冰冷而精明的深色双眼时,男人前一刻的愤怒此时已经化作了纯粹的恐惧。那双眼眸之中充斥着和阿提密斯·恩崔立稚嫩的年龄全然不相称的邪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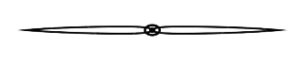
当天下午的晚些时候,阿提密斯特步出巴沙多尼公会的大厅,去完成一次被耽搁多时的短途旅行。他回到属于他的街道上,回到他在卡临港的污秽中开辟出来的王国。
随着灰蒙蒙的橙色落日宣告着又一个酷热白昼的终结,阿提密斯转过街角,进入自己的领地——那个暴徒也曾转过相同的街角,然后丧命在阿提密斯的手中。
阿提密斯摇了摇头;发生的一切都令他感到难以接受。他在这些街道间的严酷环境中活了下来,在西博斯·罗尤赛特横加在他身上的挑战中活了下来,而且,在他为此做出的反击中活了下来。他活了下来,不断成长,如今已经成为了巴沙多尼公会正式的公会副官。
阿提密斯缓缓踱过泥泞的小巷,目光左右逡巡,正如他统治着这里时一般。当这些街道还属于他的时候,生活非常简单。但现在,道路已经呈现在他面前,引领他走进他奸诈阴险的同行中间。从此之后,他将不得不背靠墙壁行走——经他检查没有致命陷阱和传送密门的坚实高墙。
就在短短几个月间,种种事件纷至沓来,降临得如此迅速。他从一个街头的流浪儿一跃成为卡林港最强大的盗贼工会,巴沙多尼工会的公会副官。
然而,当他回首观望那条将他从曼农带到卡林港,从泥泞的小巷带进盗贼工会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厅堂的道路时,阿提密斯·恩崔立不禁暗忖,或许这种改变并没有多么神奇。并不曾发生什么突如其来的变化;他之所以能够攀上今日看似显赫的地位,靠的是对街头生存技艺年复一年的磨练,靠的是岁复一岁地挑战并击败残忍的对手——例如西博斯,或是商队里的老色鬼,又或者是他的父亲……
旁边传来的喧闹声将阿提密斯的注意力转向一条宽阔的街巷,一群男孩儿从那里穿过。在这帮蓬头垢面的小家伙中,一半人正在来回扔着一块小石头,另一半则试图抢走它。
突然之间,阿提密斯震惊地发觉他们都是他的同龄人,甚至比他还要略微年长。而在震惊之中,他同样感到一阵不容忽视的痛苦。 男孩儿们环笑着、叫喊着,很快就消失在了下一个棚屋之后,只留下了一团扬起的尘埃。阿提密斯立即将他们抛诸脑后,再次思忖着他已经取得的成就,思忖着那些依旧铺展在他面前的荣耀和权力。毕竟,他付出了自己的稚龄和纯真才换来了拥有这些黑暗梦想的权利,而直到付出之后,他才领悟到它们真正的价值。
[1] 《第三阶》一文最初刊录于1994年出版的《恶名国度》,后收录于2011年出版的《崔斯特系列短篇集》。在《恶名国度》里,作者选择用“阿提密斯”称呼还是孩子的恩崔立,但在《崔斯特系列短篇集》中,作者改用了姓氏。本文依照2011年的版本翻译。
[2] 前文曾出现“西博斯,连同剩下六名公会副官”的措辞,公会副官的数目与此处矛盾。原文作:“Theebles along with a half-dozen other lieutenants…”译者英文不精,亦不排除half-dozen(半打)有作虚数使用的可能。
| 上一篇 | 目录 | 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