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eff Grubb
翻译:零与地下城
| 上一篇 | 目录 | 下一篇 |
我坐在斯科努贝尔恶心的食腐兽的阳台上,在昨天晚上的和即将来临的宿醉之间徜徉,脑袋里思考着“应该留在床上”。这话说的很对,也许是在度过一个因为火球、闪电或其他玩意而变得格外糟糕的早晨之后,由某位施法者率先提出的。
不过这对我没什么用,因为在除我以外的一切狂奔向南[1]之前,我原本就躺在床上。
让我来解释看看。在三点的钟声敲响之前不久,你忠诚的特提斯·万兹,正在食腐兽三楼的头等间里伴随马厩的味道幸福地入眠。食腐兽是在上一期瓦罗指南发售后突然冒出来的新店,由于瓦罗向旅行者的大力推荐,很多地方已经不再受本地人的欢迎了,于是新的酒馆,餐馆和冒险者们的集聚地应运而生。安普曾经一度建议最好就跟在瓦罗的屁股后面开新店,因为他提起的那些店总是很快就会被攥着那本可恶小册子的法师和战士挤爆。
我离题了。我只是在给故事设置背景,打理舞台,奠定基础,三点,卧室,食腐兽。
然后天花板爆炸了。
好吧,也不能完全说是爆炸,但从上方传来的雷鸣声就和房顶塌了没什么两样。我猛地坐直,注意到我的床——一张结实的四脚铁木床——正在摇摆和跳跃,活像一条神经质的食腐虫。房间里每一样没焊在地上的东西,从尿壶到铜镜,都加入了这场震颤的末日之舞。
任何还有理性的人都会做出和我一样的事——躲进被子里,向任何愿意倾听的神祇祈祷,保证我再也不会碰龙息啤酒和死亡奶酪。
“特提斯·万兹!”一个熟悉得吓人的声音从天花板上传来。
我从毯子里露出一只眼睛,看到了马斯卡叔公火红的脑袋。我毫不怀疑他的脑袋还跟他深水城里的身体连在一起,这一定是他送来的星界啥啥[2]或者幻影某某的法术,这时的我怕得要死,根本不关心。
我抬起头,勇敢地面对深水城最伟大的法师,“这不是我的错!”我大喊道,把床单拉下头顶,希望他能听清我说的话。“我不知道她是淑妮的祭司,没人告诉过我那家会馆的事,我是无辜的!”
“别管那些!”叔公声若雷霆,“我有重要的事要你去做!”
我从被子边缘偷偷看去,微弱地挤出声音:“我?”
“你。”叔公不耐烦地说,他的不满全然写在脸上。“我的一件神器,耐色瑞尔的遗物,被偷走了。”
“不是我干的!”我立刻插嘴,“你问过马库斯表哥了吗?他老是拿不属于他的东——”
“闭嘴!”漂浮在我床柱上的火红、巨大的脑袋吼道,“我知道是谁拿走了它——一个叫瑞文的小贼,正朝你这儿走来。我要你把它拿回来。那东西看起来像是三个互相嵌套的玻璃球,把它带给我,你就可以回到光辉之城!”
“好吧,这就是问题所在,”我大着胆子说,“其实我正在思考,要在更广阔的道路上开始新生活——”
“去找汉吉斯的三重法球!”幻影叔公说,“现在就去!”
说完,马斯卡的头噼里啪啦地爆炸了,成功地在墙上留下了烧焦的痕迹,顺便打碎了水罐。马斯卡叔公从不喜欢安静地离开,实际上,在我认识并躲开他的这么多年里,他从来没有走过大门。
我穿着睡衣,摇摇晃晃地从床上爬起来,收拾好打碎的水罐。我想要把这一切当成奶酪引起的噩梦或幻觉,但所有这类念头都和水罐一起碎了一地。马斯卡叔公想要某种东西,而且他希望我去搞到手。
所有人都不该让他的叔公感到失望,更别说这位叔公还能把他变成蟾蜍了。
所以,我叫来了我的巨灵,安普拉汀。嗯,叫来这个词不太好,我摩擦着戒指,手指在上面划过,将他召唤出来。
让我先说清楚:我没有一丁点的施法能力,这让我成为万兹家族的异类,被法师,术士,巫师之类各种各样的施法者的阴云所笼罩。不过,幸好我有一只风巨灵,他依附于我几年前在深水城下水道里发现的戒指上,但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好像一座在沙漠中凭空浮现的幻影城堡,安普拉汀飘然而至。气巨灵这个种族天生聪慧过人,而安普又是其中最聪明的,他每立方英寸的脑细胞比费伦任何生物都多。
安普穿着平常的衣服,蓝色的长袍衬托出他红色的皮肤。他的发髻油亮整洁,好像马尾一样,从无檐小帽下探出;他的胡须也同样一本正经,勾勒出端正的嘴唇。
“嗯哼,安普,”我说,“你听到了吗?”
“就连至高森林的德鲁伊都能听到,我十分确信,”安普平静地说,他的声音好像山下地城的空洞一样深沉,如同半身人的赌咒一样流畅。“看来你的叔公需要你。”
“需要一个工具。”我嘀咕道,四下寻找我的裤子,安普大手一挥,那条不见了的裤子便出现在他护理得当的手掌之中。巨灵是如此美妙,每人都应该拥有一个,不过在被自己的血亲恐吓过之后,我暂时没有心情来列举我的巨灵的优点了。“他为什么需要我?”
“我会尽力找出答案,”安普的回应依然流畅,“也许会需要些时间。”说完,他飘然离去。管家,仆人和守卫会乐意花大价钱学习巨灵飘逸的身姿。
我试图重新入眠,可一旦你在床上经受过家族族长魔法投影的威胁,睡眠的幸福感就会离你而去了。作为代替,我来回踱步,忧心忡忡,坐在窗沿注视围栏里的马儿,并且惊叹于他们简单的生活。
清晨来临了,而安普没有回来。我把肉汁炖蛇(至少我觉得是这个)吞吃下肚,接着走进食腐兽的厅堂,要求侍者每半小时送来一次龙息啤酒,直到我再也无法送还空酒杯为止。为了避免前一个晚上即将袭来的宿醉,我决定直接开始迎接新的酒精。
恶心的食腐兽已经有些破旧了,它的前身是一家杂货店,被奥罗拉和她的目录[3]逼得关门大吉。一楼与二楼间相距甚远,形成一个宽阔的露台,正适合斯科努贝尔的主要娱乐——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以及观察楼下街道上做着同样事情的人们。在过去的两周里,我两件事情都没少干。我已经准备好了作为原深水城住民的新生活,沐浴在这儿的阳光和酒精下,告诉别人生活在深水城这样的城市里会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整整一半的贵族都是法师,而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彼此的亲戚。
当然,现在我为自己没有离开斯科努贝尔而暗暗自责不已。安普曾在一周前强烈建议我们继续前进,但我表示反对,我可不想像我的表兄弟们那样被仆人、管家和魔法小造妖们控制。我在那时告诉安普,如果我要离开深水城、开始流亡生活,没有比呆在老食腐兽的阳台上看着商队来来往往更美妙的选择了。但斯科努贝尔距离深水城的贸易之路不过几百英尺,显然还不够脱离马斯卡叔公的手心。
当我终于注意到右手边多了一位年轻人,而且并非一直为我上酒的好心女招待时,我的胡思乱想便打断了。时间肯定没到中午,我想道,也不可能正在换班。否则,他应该会拿出一份午餐的菜单。
我勉强让布满血丝的眼球聚焦在他身上,发现新来的是位半身人,端着放在银盘上的啤酒。他的脸埋在手艺糟糕的草帽下面,朝我微笑,露出一口白牙。我眨了眨眼睛,他仍然没有消失,于是大胆地与他攀谈起来。
“啊哈?”我问道,这已经是此刻我所能表现出的最聪明的样子了。
“劳烦了,老爷,”小个子的半人说道,扯下他的草帽,露出一头乱蓬蓬的红发。
“但我想问问您是昨儿睡在楼顶的那位不?轰隆轰隆、噼里啪啦的那个?”
此刻的我无比希望自己能够拥有某种魔法天赋,能够通晓语言,或是领悟方言,或者其他随便什么能够派得上用场的玩意。但我最后只是选择了一种久经时间考验的回应:“啊哈?”
半身人毛茸茸的脚不安地挪了挪,“那啥,老爷,我在外头听到了很多,有个大动静说您要去追捕瑞文。”
我点点头,十分缓慢,我希望自己看起来能更睿智些,但实际上我更担心肩膀上那个甜瓜似的东西会掉下来,在露台里打滚。“那么你是……?”
“卡斯帕·米利多克,为您效劳。”半身人继续道,“我自己也在抓那个瑞文,但我想,您这么厉害,声音还这么大,大可以帮帮我这样的小个子,我们一起抓贼。”
“噢,”我说着,把乱糟糟的想法抛回脑海深处。“你为什么要追捕瑞文?”我还没有醉昏头,清楚地知道半身人做事至少会有三个理由,而其中至少两个会违反几条当地法律。
半身人低头看他的毛脚,“那啥,瑞文也光顾过我的家里,我得把东西找回来,否则就回不去了。”
即使有酒精的影响,我的心还是向这个小个子敞开了,他和我处于相似的境地。“瑞文从你那儿偷了什么?”
“钱,老爷,”半身人答得很快,“所有的钱,孤儿院的。”
“孤儿院?”我摇摇头,“刚刚你还说是家里。”
“的确,老爷,”半身人用力点头,“我们家的所有人都是孤儿,不幸极了。”
“的确。”我喃喃自语,不理解半身人真正的目的。当然,安普拉汀不在附近,而时间已经接近正午,如果我能在平时的帮手不在的情况下搞定这件事,巨灵和我的叔公就会明白我到底有多么精明。
“很好,”我说,“带我去见瑞文,我们来面对面地解决问题。”
“噢,那可不行,”半身人含糊其辞,“瑞文不是人类,而是变形怪,他想怎么变就怎么变。我想我能找到他,但您得做好准备,等我喊您的时候跑得快点儿。您能帮帮我吗?要不然,就当是帮帮其他孤儿?”
他抬头看我,眼含热泪,当然,我只能答应。这是件高尚的事。况且这小个子知道该怎么找到瑞文,我的工作也可以轻松不少。
我从半身人的手里接过啤酒,但没有喝完,新端来的杯子也被原封不动地送了回去。
我转而要了一本手写本和笔,还有一些其他的文具。当安普出现时,我正在给马斯卡叔公写信,告诉他一切都在控制当中。前一刻我的左侧还空无一物,而下一秒,他来了——优雅得一如既往。
“我相信你一定有了新发现,”我呵斥道,宿醉的影响迟到地显现出来,“你花了大半个上午的时间。”
安普的腰弯下四分之一,“万分抱歉,特提斯大人,”他说,“我花了些时间才查清这个装置的性质,以及到底发生过些什么。我最终和你的叔公用来清理烟囱的小精灵搭上了话,她显然目睹了这起骚乱的大部分经过。”
“好吧,说说看。”我说道,不耐烦地用笔敲打着纸面。
“三重法球是耐色瑞尔的神器,”巨灵将双手背在身后,活像开始背诵功课的学生。“耐色瑞尔是一座法师的国家,远在数千年前,科米尔或深水城兴建前便已经衰落。据说,这些法师中最弱的一个也比如今国度中最强大的施法者更加伟大。”
“一座由无数个马斯卡叔公组成的国家?”我控制不住自己的哆嗦,“难以置信。”
“确实如此,大人。”安普拉汀说,“三重法球显然是那个国家里最强大的兵器,因为它能够杀死周围的所有魔法。没有火球能在它身旁爆炸,没有召唤能够奏效,任何防护都会消失,魔法武器的威力也荡然无存。你知道这在法师王国里会是多么有用。”
“是的,”我说,“如果靠近它,他们就会变得像小动物一样柔弱。”
“正是这样,”巨灵说,“因此,在耐色瑞尔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它都被法师藏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其他法师则雇佣战士将它从藏匿处追回。就这样,它跨越了大半本耐色瑞尔史书,直到王国灭亡。十几年前,一队冒险者在埃诺奥克沙漠发现了它,你的叔公立刻意识到能够摧毁魔法的神器的危险性,他将它得到手,并将其锁在最深的地牢里。”
“远离窥探魔眼和其他法术。”我插嘴道。
“没错。就我所知,这件神器是一组三个、互相嵌套的水晶球,由虹晶打造,看起来像是肥皂泡。和所有神器一样,它无法被用通常的方法摧毁,所以你的叔公把它锁在了一个安全的地方。然而两周前,一个叫瑞文的盗贼从那个安全的地方偷走了它,显然,他正沿着贸易之路走来,前往斯科努贝尔。”
“也就是马斯卡叔公要我找回那玩意的原因。”我说。
“原因之一,”巨灵说,“你是这个家族里为数不多没有魔法天赋的人。也许他认为如果你完全不通魔法,风险就会更小一些。”
“或者说要是我死了,损失也会更小一些。”我嘀咕道,“好吧,起码你会帮我。”
安普拉汀脸色苍白,这对巨灵来说还真是少见。“我担心自己帮不上太多。这个反魔法领域会解除区域中的任何召唤,也包括我。实际上,它的反魔法性质也阻碍了魔法的探测,也许将这件事告知地方政府对我们而言会更好。”
听到这个消息,我皱起眉,“地方政府,”我不屑地摇摇头,“如果这样的东西落在他们手里,他们一定会把它锁起来,严加看管,然后马斯卡叔公会对我大发雷霆,直到下一次的动荡之年。不,我们可以自己动手。”
“但是大人,反魔法的性质意味着……”
“没有但是,”我举起手,“当你还在浓烟中盘问壁炉里的小东西的时候,我也在勤奋地钻研自己的手段。就在此刻,我的探员也在城中搜寻这个叫瑞文的家伙。”
“你的——”安普拉汀看起来十分震惊,好吧,就像一个气元素组成的生物所能够表现出的那样震惊,“探员……?”他艰难地将这个问题转化成陈述句,但没有完全成功。
“没错,”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这点小事我会自己解决,不再需要你更多的参与。”
“大人,我……”
“嘘,嘘,”我摸了摸额头,两次宿醉姗姗来迟,如今一起涌现上来。“既然你说帮不上忙,我不会强求,相信万兹家族的直觉吧。”
巨灵看起来有些怀疑,但他还是说道:“如你所愿,大人。”
我对着气巨灵微笑,这段关系的主宰者毋庸置疑。“不过可以的话,请做一份你的特制煎蛋饼,当做酗酒后的补品。如果整个国度不再跟着我的心脏一起震动,我感觉会更好一些。”
安普拉汀想要提出某种警告,但他只是说:“当然,大人。”他飘离了我的视线。
我站在食腐兽的露台上,扶着栏杆,试图装出一副沉思的模样;但实际上我度秒如年,等待安普回来治愈我严重的头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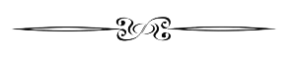
“那是瑞文?”我问半身人,“可她是个女人!”
“小声点!”破旧的棕色长袍下的矮个子压低声音,“如果她是个女人,那我就是条红龙。她是个变形怪!如果你再大吼大叫、把眼珠子瞪得像鱼那么大,她会发现的!”
那个不是女人的女人坐在拥挤的大厅对面的桌子上,身穿旅行皮衣和蓝色的斗篷,正好面向我们,让偷窥变得更加困难。一只旅行包放在她身旁的桌上。她朝我们的方向漫不经心地瞥来,我立刻缩回自己的棕色斗篷和兜帽里,略微转过身,尽可能地不让自己像鱼一样瞪着她。
坐在她身旁的同伴可能是位山丘巨人,也可能是位食人魔,因为他几乎和安普一样高大。那位同伴也穿了一件足以囊括万物的斗篷,呈深红色,使他看起来就像是对面桌子上的一轮超大号的落日。
我们所处的地方是疲惫的独角兽,很不幸地,前文所述的瓦罗指南使它引起了注意,后果就是这里现在挤满了新来的,旅行者,老练的雇佣兵和纯真的潜在冒险者们。由于独角兽恶名远扬(这是瓦罗的说法),人人都穿着厚重的斗篷和兜帽,使这里看起来就像是幽灵,缚灵和鬼魂的聚会。
瑞文是个例外。她——我是说它——摘下兜帽,金发像啤酒一样洒在肩上。她看起来似乎有着精灵的血统,耳朵微尖,纤细的下巴线条画出一道柔软的圆弧。我不得不提醒自己这一切都是幻觉,她——不,它——是一只变形生物,只要它想,大可以变成亚戎国王或是马斯卡叔公的样子。变形怪真正的外貌是细长的人形,没有性别,没有毛发,全身浅灰。总而言之,这不是个令人高兴的想法。
瑞文与身旁的大号落日热烈地交谈着,她的眉头一度蹙起,纤细的手掌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行李。我们离得太远了,听不清他们的对话,但是显然,他们在讨价还价。
不需要伟大的法师也可以搞明白他们的交易对象。包裹的大小和形状足以装下法师的水晶球,或是古代的三重法球。
落日的话语似乎让她平静下来,脸色恢复如初。她侧耳聆听,点了点头,提起包裹大步走向门口,而落日纹丝未动。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但当她走到门口时,变形怪转过身,和我对视了短短一瞬。我不确定那是否是我的错觉,但整个世界仿佛天旋地转,以全新的方式运作起来。
接着她——它就走了,我转身,注意到那轮巨大的落日也不见了,也许他回到了秘密房间里,里面还有一群赛尔的红袍法师。
“快来!”半身人急促地说,“再不动弹就跟不上她了!”
我的盟友也用女性代词称呼我们的目标,这使我稍微松了口气,跟着那个藏在斗篷下的矮个子走出独角兽。我们的离开没有引起任何注意或骚动,但我们还是戴上了兜帽。
夜晚像个醉酒的矮人一样晃晃悠悠地来临了,街上几乎空无一人。那些没心没肺的家伙已经缩在被窝里(除非他们也被魔法叔公打扰),然而塞伦涅却盈满了,像灯塔一样将光芒洒在我们的猎物头上。
我们跟踪她来到河边的一座住房前,一个龇牙咧嘴的食人魔拒绝我们进入,但几枚金币确实地买到了这位年轻女士(她自称德玛蕾斯特)的情报。她刚到,和那只旅行包形影不离,住在二楼,靠近酒馆后方的地方。
就这样,在马斯卡叔公初次露面的几乎一整天之后,我穿着宽大的长袍顺着窗沿走去,身后还跟着一个类似打扮的半身人。周围平原上吹来的风轻敏急切,有好几次我都不由得担心斗篷会裹着我们头重脚轻地随风飞起,好像断线的风筝一样盘旋在斯科努贝尔建筑群的上空。
我在这天晚上头一次后悔给安普放了假。他对于我找寻死魔法神器十分不安,所以我让他离开了。现在也许他正躲在某个商人的图书馆里,阅读着什么《央地的历史》或者《奥巴斯基[4]一脉罗曼史集》,而他的主人正在准备一场非自愿的飞行。
正因如此,进展缓慢。如果我们靠近酒馆的前部,毫无疑问会被全副武装的守卫发现;我们不得不在有路人靠近脚下的巷子里时伪装成石像鬼,其余的时间则朝着我们的目标——一扇亮着的窗户前进。当我们靠得更近时,那扇窗户的灯光熄灭了,我们等待了很久,以确保那位假冒的德玛蕾斯特并不是为了警戒屋外才关闭灯光,接着又继续我们艰难的行军。
窗户上了锁,英明的保护手段,哪怕这间屋子位于斯科努贝尔的二楼。半身人卡斯帕取出一根细长的金属丝,嵌进两扇窗户之间的缝隙里,轻易地弹开了窗闩。
“进去吧,伙伴。”半身人低声道,笑着露出一口白牙。
“我?”我轻声回答,“我以为你们这些半身人才更擅长潜入别人房间一类的事情,毕竟你们离地面更近。”
半身人发出不满的哼声,“好吧,我是可以,那么你就接着站在窗沿上,等待条子把你摘下来。当然,如果这就是你的选择的话……”他不再作声。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同时我也意识到,如果我还想要三重法球,最好在他之前拿到手。
我尽可能安静地遛进房间,斗篷减轻脚步的能力被它本身的笨重所抵消。月光洒进房间里,只留下幽蓝的光斑和黑檀色的阴影。那个名叫德玛蕾斯特,或者说瑞文的变形怪盗贼正躺在她的床上,被褥外的长发在月亮的照耀下泛着银色的光芒。
旅行包放在床对面的矮桌上,也许它装着法球,或者半身人的金币,又或者二者皆是。打开包裹检查一下总会有收获的,我想,如果半身人的金币不在那里,至少我可以说服马斯卡叔公来补偿他们的经济损失。
包裹的金属扣咔哒一声打开了,它在桌子上敞开,接着咔哒声再次响起。我原本以为是回声,但接着身后传来了一个冷冰冰的女人声音:“离那个包远一点,否则我就把你从那儿丢出去。”
作为法师家族里的异类,我天生就擅长服从命令。我把旅行包放在桌子上,向后退了两步,双手高举。我没有把包锁上,但只是因为没有人要求我那样做,而不是出于任何好奇心。那里面闪烁着水晶的光芒,没有金币的影子。
“现在,转向我。”那个悦耳的声音说道。
我缓慢地转过身,注意到窗户旁卡斯帕的剪影。我尽力不让自己畏缩,希望他已经为这种可能性做好了规划,坐在床上的女人似乎还没有注意到他。变形怪举着一把弩,是那种卓尔打造的手弩,看起来十分危险。她将它对准我,然后把被子踢开,被子下面的她衣着整齐,我松了一口气,又感到一丝遗憾。
她冰冷地盯着我,“这伪装比平时还蠢,瑞文。”她说,“你为这张脸杀了一个贵族家的公子哥?”
“对——对不起?”我勉强开口,脑子里一片混乱,“抱歉,我不是瑞文,我还以为你是——”
我犯了个错,手臂放低了一点,瑞文将弩对准我的胸口,我立刻重新举高双手。
“别动,变形怪,否则我就在你身上钻一个新洞。”
“抱歉,”我说,不知道安普是否能在他藏身的图书馆里听到我无声的请求,“但我不是变形怪,你才是,如果你也搞不清楚状况,也许我们应该谈谈,而不是在任何人或者任何东西上钻洞。”
不是瑞文也不是变形怪的德玛蕾斯特放声大笑,她的声音清亮,却冷酷而残忍。她的手弩正冲着我的脸,而我闭上了眼睛,我不希望自己看到的最后一幕会是朝自己飞来的弩箭。
弩箭离弦的声音响起,可令人惊讶的是没有疼痛,甚至没有与死亡擦肩而过的微风,
取而代之的是女人低声的诅咒。我深吸一口气,确认自己仍然活着,然后睁开眼睛。德玛蕾斯特跌回床上,左手紧握住插在她右肩上的箭矢。她的右臂虽然还在,却一动不动,我没有再看到那把手弩了。血液顺着她的手臂流下,染黑了她蓝色的长袍,在床单上留下一汪红色的水洼。
我转过身,看到卡斯帕缓慢地跨进室内,他自己的卓尔手弩已经装上了另一支弩箭。
我有些恼怒,于是开口:“你还打算等多久才露面?”但半身人的弩立刻对准了我的脸,就像早些时候德玛蕾斯特做的那样,显然,这就是今晚的主题了。
“走到女人那边去,蠢货。”半身人用一种非常不半身人的声音叱喝道,他的声音变得尖锐,好像折断的枯枝,显然十分习惯发号施令。
我朝那个女人走近两步,她仍然坐在床上,呼吸凌乱,她的眼神开始变得呆滞。
“毒药,”半身人说着,向桌边走去,弩箭始终紧紧地锁定在我身上。“不是发作最快的,但够用了。你很快就可以尝尝看。”
在半身人移动的同时,他的身体开始像蜡烛一样融化并伸展拉长,我知道蜡烛不会拉长,但卡斯帕的确是这样做的。半身人肉体的脂肪融化了,漆黑的斗篷变得暗淡,他的脑袋缩小,眼睛变成白色,瞳孔也消失了。等半身人走到桌子旁边,他已经不再是半身人了,他变成了一只实打实的变形怪。
“你就是瑞文,我猜。”我说道,竭力控制住声音中的颤抖。
“完全正确。”这只生物说道,用自由的那只手在旅行包中翻找。他掏出一个巨大的水晶球,第二个水晶球漂浮在里面,它的里面又漂浮着第三个球。三颗法球在月光下闪着微光。
“你帮了我很多,特提斯·万兹。”变形怪微笑道,甚至再次露出一口白牙。“是你帮忙转移开我昔日伙伴的注意,好让我可以先发制人,现在你又将再帮我一次。等守卫在这里发现你们二人的尸体,他们会认为这位女士被强盗吓了一跳,你们同归于尽。至于三重法球的新主人,则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我试图解释我可以为法球出一个高价,但一声低吼打断了我。床上的女人行动很快,比我在类似情况下的动作要快得多——半夜,卧室,肩膀上还插着一根毒箭。在瑞文和我交谈的时候,她已经蹲伏下来,如今正朝变形怪扑去。
变形怪没有料到他的昔日伙伴能够摆脱毒药的影响,弩箭还对着我的方向。他迅速地转换目标,射出一箭,却偏离了目标,在女人猛撞向他的时候刺进墙里。法球像活物一样从他的手中脱出,在月光下飞旋。
我奋力扑去,好像它是丰收节宴会上的最后一餐;我的理智告诉我,在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岁月之后,一次摔落不会损坏这件神器,但马斯卡叔公的身影却在我的心里阴魂不散。我的心要我拼命伸直手臂,好在落地之前接住它。
我在离地只剩几英寸的地方把法球抓在手里,和它一起向侧面滚去,远离战场。等我起身时,远处的喊叫和开门的声音此起彼伏,显然,这场战斗已经吸引了其他人的注意。
那两个盗贼,人类和变形怪,正在房间中央缠斗。变形怪在战斗过程中已经变成了德玛蕾斯特的样子,所以她们看起来就像一对抱在一起打滚的金发双胞胎,互相抓挠。
我看了看她们,又看了看手里的法球,然后又看了看她们,想知道自己有没有可能越过她俩走出房门。我实在不想再从窗沿边走一次了。
就在这时,房门突然被打开了,露出来三位,也可能是十几位守卫。他们每人都扛着一把沉重的双手弩,能够一箭刺穿马厩墙壁的那种。有些人还举着火炬或提灯,而在他们的身后,站着那个身穿深红色长袍的大号落日。
两位身处战斗当中的德玛蕾斯特分开了,她们站起身,盯着新来的人。我小心地后退,窗户似乎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落日伸手拉下他的兜帽,露出一张熟悉而平静的脸庞。
安普拉汀,当然是他。我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又恢复了跳动。
守卫们不如我那么肯定,他们的弩箭在两位双胞胎中打转,不确定哪一位才是真正的危险人物。两个盗贼不安地起身,试图与彼此拉开几英尺的距离。
我尖声道:“受伤的那个是真的,没受伤的是一只变形怪。”
没有受伤的那一位,卡斯帕、瑞文和变形怪,原地转身,冲我嘶吼。他的尖牙变得细长,巨大的翅膀从肩上萌生,他冲我一跃而来,想要将我当成人质,法球会是他的战利品。
两件事同时发生了。我把法球上抛,朝大门和安普扔去;与此同时响起三声,或十几声弩箭的脆响,变形怪应声倒地。
神器像肥皂泡一样穿过房间,最后落在安普的手里。
安普看了我一眼,腰弯下四分之一向我行礼,接着松开捧着法球的手。
它重重砸在地上,彩色的玻璃片四处飞溅。
我恐怕也紧随其后,昏死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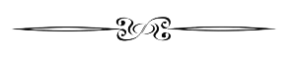
回到恶心的食腐兽的露台上,我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足以欣赏从斯科努贝尔破烂的建筑上冉冉升起的太阳。
“你大可以提前警告我的。”我噘着嘴喝酒,气巨灵又取出一块湿毛巾,敷在我滚烫的额头上。“你并不想要任何警告,”安普说,“我尽己所能地处理了这件事。我告诉当地的卫兵,你从一开始就知道半身人是变形怪,并且配合他们找到了失踪的神器,因此你在这件事上无可指摘。变形怪已经死了,而他过去的搭档,盗贼德玛蕾斯特中的毒已被清除,正在准备接受镇上的审判。”
“你是怎么知道的?”
“准确地说,我不知道。尽管我觉得你得到偶然的援助这件事很有趣。只要和食腐兽的侍者稍作交谈,就能得知你的帮手是一位半身人,而在斯科努贝尔找一位戴着草帽的红发半身人并不困难。我注意到他在盯着一家特殊的酒馆,于是在那儿声称我是一位法师,正在寻找一件特殊的神器。德玛蕾斯特希望能在被同伴追上之前卸货,于是联系我在酒馆见面,也就是你见到我们的地方。那时候,她正打算把那件假神器卖给我。”
我的大脑被打击过度,疲惫不堪,饱受威胁。我犹豫了一下,问道:“假神器?”
“当然了,”巨灵说,“正如我冒昧地以你的名义向守卫的解释,如果它真的是传说中的那件神器,那么像我这样的召唤生物原本就无法靠近它。既然我能和它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就足以证明这是假货。它只是将水晶和不同密度的气体组合在一起,这样就能使每个球体在更大的球体里漂浮了。在那次见面里,我故意没有带上她想要的金币,从那里提醒守卫德玛蕾斯特的房间被人闯入会比较容易,最终,我们及时赶到。”
我摇摇头,“假神器?那么是变形怪把真正的三重法球藏在别的地方了?”
“瑞文恐怕也不知道这是件赝品,所以他才如此努力地驱使你作为他的棋子。而德玛蕾斯特,如果她有真正的法球,就会让瑞文带走这件假的,让他信以为真。他们都没有时间去制造赝品。”
“那么是谁做的?”我说,“不可能是马斯卡叔公。”
“我恐怕你叔公的担忧也是货真价实的。”巨灵说。
“如果不是盗贼,也不是马斯卡……”我灌了一大口酒,“马斯卡叔公从来没得到过真正的三重法球,对吗?”
“我是这样想的,”巨灵说,“毕竟,你要如何测验一件据传能抵御所有魔法的物品的魔力?”
我露出笑容,这是过去十二个小时以来的第一次,“所以马斯卡老叔公在最开始就被耍了。”我想到这里,咯咯直笑,“真想看看他收到我的说明信时脸上的表情!”
安普拉汀郑重地低咳一声,在他完全不同意我的话、又不能直说时,总是会发出这种咳嗽。我把视线投向我的同伴,而他抬起头,看向远方。
“如果你的叔公从来没得到过这件神器,”他严肃地说,“那就意味着他现在非得到它不可。还有谁能比已经得到过一次赝品的人更加适合这项任务呢?”
我让这句话沉进被啤酒浇透的大脑,“所以他得到消息的时候我们最好不要留在这里,是吗?”
“正确。”
“噢,好吧。”我叹着气,喝光最后一杯啤酒,将空酒杯放在它的同伴身旁。“看来在斯科努贝尔的旅居生涯就到此为止了,我想我们需要搬到更远的南方,离深水城更远一些。”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安普拉汀说道,以流畅的动作取出我们的包裹,“所以我已经擅自购买了车票,我们一小时后出发。”
[1] 指事态变糟
[2] 星界投射Astral Projection,后面的幻影可能是幻影之力Phantasmal Force
[3] 2E 扩展书,奥罗拉的国度目录Aurora’s Whole Realms Catalogue
[4] Obarskyr 科米尔王室
| 上一篇 | 目录 | 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