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罗伯特·金
翻译:零与地下城
如果从大冰海袭来的风暴常会带着不受欢迎的东西来到高耸的凯帕尔布里格,而今晚,除了狂风和暴雪,它还带来了一个面目可憎的恶人。
当他轻轻推开怒啸芦苇的破门之时,还没有人意识到他的本性,他们只是看到一个身穿漆黑兜帽的高大的陌生人站在飞旋的雪花里。他砰地一声关上身后的大门、让后者在门框里发着抖,离门最近的人不禁因狂风和唐突出现的人影向后畏缩。陌生人没有管灌进靴子里的冰雪,而是蹒跚地踏过酒馆锃亮的地板,走到颤动的壁炉跟前。他弯下腰,往火堆上扔了几根木头,接着站起身,遮住了那团温暖,在房间里投下一道巨大的阴影。怒啸芦苇的所有眼睛都偷偷地投向这个残破的人影,小酒馆里的谈话声渐渐减弱了。
从炉火映出的轮廓看来,陌生人就像一只畸形的巨型木偶,他只有一只胳膊,右边的袖子别在肩上,只有左手负责打理这具恶臭的身躯。那只落单的手现在正有意无意地向下拉扯长袍,然而下面被浸湿的身体看起来还是那么不成样子。他的动作时而变幻,但始终没有摘下头上的兜帽,那颗头看起来几乎比躯干要小上两圈,在风帽之下露出来的脸庞苍老而暗淡。他留着一道黑色胡须,嘴唇冰冷僵硬,鹰钩鼻。总而言之,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藏在这堆长袍里的大高个子,原本是脸庞的位置却顶起了一颗比例古怪的木偶脑袋。
然后他开口了,空洞刺耳的嗓音让酒客们心惊肉跳,“你们中有人愿意掏钱多买一碗血汤和麦酒吗?”
除了茫然、回绝的目光之外,没有任何回应。吧台里面的霍勒斯也不愿给陌生人端出哪怕一杯水。显然,这些人宁可承受他的愤怒,也不愿大发善心为他提供一些食物。
陌生人显然对这种反应再熟悉不过了,他缓慢地摇了摇头,发出枯叶似的干笑。他踉跄地走向一把椅子,它在他最初进门时便腾了出来,如今仍然残留着之前的温度。他跌坐下去,像破损的风箱那样喘着粗气。
“在我的家乡,索萨尔,一个好故事总是可以换来鲜血与烈酒。我碰巧就有这样一个故事,那片土地上诞生过最伟大的英雄,也许他的故事可以为我换来一丝温度。”
那些原本打算用赤裸的鄙夷和冷酷的沉默将他驱逐的人们现在纷纷转过身去,彼此窃窃私语;霍勒斯则穿过他身旁摇晃的大门退回厨房里,来到灰色的洗碗水和成堆的锅具旁边。
残破不堪的流浪者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他用发青的手指打了个响指,接着开始讲述他的故事。绿色的火焰凭空燃起,在他周身飞旋,好像一只柔软的手掌从最深邃的黑暗里向外伸展;火花的轨迹映亮了所有坐在餐厅里的面孔,而每一粒闪光最终都熄灭在酒客眉头间油腻的肉褶里。
窸窣的魔法最终被一声低沉的叹息所取代,很快,这个地方重归寂静,故事开始了。
“索萨尔的土地上曾经有一位守护者,他名为帕拉莫尔,是一位高贵的骑士,也是有生以来最伟大的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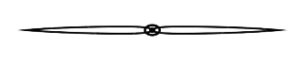
金发银眼的帕拉莫尔爵士全副武装,大步穿过凯昂国王的王座厅。其他任何骑士都会在迈过这道门槛时被剥夺武器和装备,但高贵的帕拉莫尔是个例外。他目不斜视地向前行进,手中握着破法长剑普纽玛,拖着身后的袋子,走向国王的王座。国王,公主以及一群焦灼不安的贵族停下他们的议论,朝他望去。直到长剑快要挥到国王的面前,帕拉莫尔才终于停下脚步,他单膝跪地,向他效忠的对象行礼。
国王的两鬓有着过早的斑白,他开口道:“你将绑匪抓获了吗?”
“比那更好,陛下。”帕拉莫尔回答,他起身的速度太快了,换做其他任何人都要被视作傲慢无礼。他将手伸进袋子,被他所杀的五个绑匪的头颅纠结在一起,而他正将那个庞大而狰狞的团块取出。
国王的女儿被吓得向后踉跄,直到现在,凯昂国王才注意到,帕拉莫尔爵士在穿过房间时,他拖着的袋子在身后冰冷的石板上留下了一道光滑的红线。
“陛下,现在在您眼前的头颅正是属于您所追踪的暴徒。”骑士解释道。
接下来是一阵令人喉咙发紧的沉默。巫师多索姆从大王座背后现身,他覆着黑须的嘴唇已经习惯了在国王耳边絮絮低语,“你应该把他们带回这里审问,帕拉莫尔,而不是砍掉他们的头。”“别这么粗鲁,多索姆,”国王责备道,他不以为然地挥了挥手,“让我们的骑士讲讲他的故事。”
“这是个很简单的故事,陛下,”帕拉莫尔回答,“我亲自审问了那些绑架犯,而他们什么也说不上来,于是我摘掉了他们空空如也的脑袋。”
“荒谬,”多索姆说,“也许你只是砍下了最先看见的五个农民的头,然后把他们带回来,声称他们就是罪魁祸首。本应进行一场审判。哪怕这五个人真的有罪——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了——我们也再也无法得知究竟是谁指派这些恶棍去做了那些骇人听闻的事情。”
“他们是偷走我们身边贵族孩子们的罪人。”帕拉莫尔的声音刚正有力,“如果说有什么不妥,那就是我依然太过仁慈了。”
“你阻碍了这场审判——”
“让这家伙别再胡言乱语了,”帕拉莫尔向国王要求,有力的长剑已经对准了无事生非的巫师,“或者我的勇士们会先完成这项任务。”
王座厅的大门忽然洞开,纷乱的脚步声随即传来……小小的脚,孩子们的脚,正欢快地在他们的救星身后的走廊上奔跑。他们大声喊叫着不成样子的赞美诗,歌颂他们正奔向的帕拉莫尔爵士。
看到孩子们,贵族离开高台,冲过去拥抱他们被囚禁已久的儿子和女儿。重逢的热泪和嘘寒问暖的声音淹没了多索姆的反对,他退到王座之后那个属于顾问的安静位置,仿佛他们的欢声笑语将他赶回了黑暗之中。
在这样愉快的吵闹中,帕拉莫尔笑着冲国王喊道:“陛下,我相信您欠下了我一个人情。正如在营救这些可爱的孩子们之前您向我许下的承诺,我要求牵起索萨尔境内最美的一只手;而那只手正属于您迷人的女儿,黛蒂拉公主。”
帕拉莫尔的要求得到了快乐的孩子们的认可,他们离开父母,挤在救命恩人的身边,热情地为他声援。
黛蒂拉骨白色的皮肤泛起红晕,嘴唇抿成一条深红色的线。国王的脸色因犹疑而发沉。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开口,孩子们恳求便被一声怒吼打断了。
“安静,孩子们!”一位瘦削的贵族命令道,他乌黑的发丝下同样乌黑的眼睛里燃烧着怒火,“你们幼稚的愿望不该被放到这儿说。公主的手早已许诺给我,彼时我还年幼,而她尚未出生。这个横刀夺爱的骑士——”他在说这个词时嫌恶至极,“——无法将她从我这里夺走,你们的哀求也不行。”
“他说得对,”国王悲伤地摇了摇头,他停顿片刻,仿佛在聆听来自王座之后的轻声细语,“帕拉莫尔,依照传统,我必须将她的手交给菲利斯大人。”
帕拉莫尔爵士收起剑,双臂愤怒地抱在胸前,“出来吧,邪恶的巫师,别再在陛下身后的阴影中躲躲藏藏。你的低语无法阻止我的主君及国王实现他、我还有公主的愿望。”
说完,帕拉莫尔的手抚上强大的宝剑普纽玛的剑柄,以驱散多索姆可能会对国王施展的任何法术。他打了一个响指,擦碰的指尖在空气中激起一丝火花。国王的随从及国王本人如梦初醒,转身看向藏身黑暗的巫师;多索姆紧绷着脸,回应了这次召唤,并走到了光所能及的地方。
国王举手示意事情告一段落,他表情严厉,“我已下定决心,你无法再动摇我,这只会使我激怒,所以请保持沉默。”而当他看向帕拉莫尔爵士,强硬的面容又变得柔和起来,“奉令传召下去,明天,你会和我心爱的孩子结婚。”
聚集在此的人们都欢呼起来,但是当然,除了菲利斯大人和巫师多索姆。欢呼的声音响彻殿堂,几乎将房顶掀翻。
只有一个女人哀恸的哭泣使大厅重归沉寂,“我的杰里米!”这位贵族夫人喊道,她跑进房间,手里绞着一条浅蓝的围巾。“啊,帕拉莫尔爵士!我在人群里找了又找,甚至去询问了守卫,但他哪里都不在。我的杰里米去哪了?”
帕拉莫尔爵士从国王面前原本属于他的位置上走下,他泪流满面地说道:“在刽子手们对他做出那样的事情之后,即便是我也无法拯救您的儿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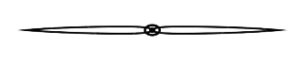
“她的哭声是那样凄惨,”穿斗篷的男人低声道,酒馆里的客人全都沉浸在他嘶哑的声音里。“甚至连邪恶的多索姆也不忍心再听下去——”
“都给我打住,谁也别再喝酒了。我不管外面的风有多大,但这里现在有一股更邪门的歪风,正从这个外来者的屁眼里往外冒!”
是霍勒斯。胖子霍勒斯在雪墩山的罅隙里照料着这家酒馆,为附近老老少少的居民提供鸡蛋和羊杂。在漫长的时间里,凯帕尔布里格的人们已经习惯了相信霍勒斯对天气、种植、政治和外人的直觉,即便如此,在这个特殊的夜晚,面对这位特殊的来客,霍勒斯好像不再是居民们那位熟识的友好知己了。
“闭嘴吧霍勒斯,”渔妇阿南莎喊道,“你根本没在听故事,还在后厨把碗碟敲得那么响,害我们得竖起耳朵才能听到。”
“就是啊。”其他人纷纷附和。
“我在厨房里听得清清楚楚,也知道这个丑八怪把蠢话当成了真理!他把凯昂国王说成是一个摇摆不定的老傻瓜,但我们都知道他坚定,公正,颇有主见。还有多索姆呢?他被塑造成一个邪恶巫师,但事实上他既睿智又善良。菲利斯大人也是一样。”
托姆的巡回牧师费尼亚开口:“我是真理的拥护者——你们对此一清二楚——但吟游诗人和酒馆老板的真实之道各有不同。所以让他继续讲下去吧,霍勒斯,而你就接着上你的酒,凭借这两者,我们才能在这个凛冽的夜晚里保持一点温度。”
这时,陌生人举起他颤抖的左手平息争执,用刺耳的声音说道:“这是你的店,朋友。你打算听从客人们的愿望,还是坚持要把我赶出去?”
霍勒斯厌恶地皱起眉,“哪怕是一条疯狗我也不会在这种天气里把它赶出去。但我宁愿你闭嘴,朋友。除了夸夸其谈以外,你还让这些人的眼睛染上了那种恍惚的古怪神情,我可不想被付了钱的客人惹出什么麻烦。”
这句话惹来了更多的抗议,霍勒斯试图平息,但他失败了。
“好吧,我就让他说。但是记住我的话,他已经得到了你们的灵魂,他用编织的语言对你们下了迷魂的魔法。至少我不会去听什么故事。”
陌生人点了点他兜帽下湿淋淋的头,注视着霍勒斯消失在厨房里。他继续讲述他的故事,眼睛却好像老鹰一样注视着一堵墙后霍勒斯所在的方向。“尽管那天早晨菲利斯大人停止了在国王、贵族和孩子们面前的自欺欺人,但在当天的晚上,穿过昏暗的城堡前往帕拉莫尔爵士的寝室时,他并不打算再度停手。”
“但在夜里行动的还有另一个孩子——死去的杰里米那可怜的鬼魂——并不打算参与菲利斯的邪恶阴谋。实际上,杰里米的鬼魂感觉到邪恶正在发生,所以一直在通往帕拉莫尔房间的楼梯上徘徊守望。当他发现楼梯下偷偷摸摸的菲利斯大人时,便连忙飞去他的故友,佩特拉的床头警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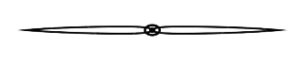
佩特拉是个棕发的姑娘,也是这群贵族孩子们的头。杰里米在城堡的卧房里发现了她,失而复得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都受凯昂国王之邀留下过夜了。可怜的杰里米伤心地注视着沉睡中的佩特拉,这双眼睛也曾经伤心地注视过他自己的身躯,同样一动不动,没有生命,没有头颅。
“醒醒,佩特拉,快醒醒。坏消息,我们的救命恩人帕拉莫尔爵士要遭殃了!”男孩的鬼魂尖叫着,他的嗓音听起来高亢而沙哑,就像一个成年人伪装成孩子时所发出的声音。
佩特拉确实醒来了,当她睁眼看到死去的朋友,少女勇敢的心猛地一惊:与那些身披薄衣的更大的鬼魂不同,可怜的杰里米没有身体可以穿戴这样的衣物。他只是一颗虚幻的头颅,漂浮在她的床头,脖颈处直到现在仍在滴落曾经喷涌而出过的红色液体。这一幕是如此怪诞和恐怖,以至于连佩特拉,这位真正的小勇士,都无法对她曾经的同伴道出一声问候的话。
“是菲利斯大人,”鬼男孩急切地说,“他计划要在今晚趁我们的帕拉莫尔爵士睡觉杀死他。”
佩特拉只勉强挤出几个音节,瞪大了眼睛。
“你要阻止他。”鬼魂的声音说。
佩特拉从羽毛床垫上爬起来,将床单披在肩上。杰里米用小男孩特有的目光——他们把小女孩同时看作他们的母亲,姐妹,情人和对手——悲伤地注视着佩特拉的双手,后者逐渐冷静下来。最后,她轻声道:“我会告诉妈妈——”
“不!”杰里米的声音急迫而强硬,“大人们不会相信的。何况,帕拉莫尔今早救了你的命,现在轮到你救他的命了!”
“我一个人阻止不了菲利斯。”
“那就把其他人也叫上,”杰里米大声说,“把班尼,莉赛尔,兰温,帕里,梅布,卡恩和其他人全叫起来,让他们带上父亲的长剑,你们可以一同拯救我们的救星,正如同他拯救我们。”
而佩特拉已经将床单的系带在胸前交叉系好,又飞快地套上了凉鞋。
“快一点,”杰里米命令,“菲利斯大人已经走上通往帕拉莫尔爵士房间的楼梯了!”
听到这件紧急的消息,佩特拉惊喘一口气,杰里米的身影闪了闪,不见了。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孩子们提高警觉,集合起来,随着佩特拉一起走上城堡的楼梯。楼梯漫长而曲折,通往帕拉莫尔下榻的高塔,路上一片漆黑,只有微弱的星光偶尔透过瞭望孔投进室内。不过当佩特拉和她的小战士们开始攀登时,他们在前方看到了一抹暗淡的烛光。
“安静。”她轻声说。
只有她年纪一半大的棕发男孩班尼严肃地点点头,小手牵起了她的。双胞胎莉赛尔和兰温互相交换了一个紧张而兴奋的微笑,而队伍后方的帕里,梅布,卡恩和其他人挤在一起,握紧了手里的刀刃。
“那一定是菲利斯大人的蜡烛。”佩特拉指着烛火,“我们必须保持安静,不能被他发现。”
孩子们点点头,他们就和生前的杰里米一样崇拜佩特拉。他们跟在她身后,尽可能地保持安静和隐蔽,尽管孩子们对于这一点的理解与成人不同。他们踮着脚尖前进,手指在蜿蜒的内壁上笔直地划过,稚嫩的嘴唇里悄声说出各种猜测。随着他们的攀爬,光线越来越明亮,孩子们的恐惧之心也越来越强,声音也因为紧张而变得尖细了。
他们就这样一路窃窃私语,所以在绕过冰冷的石梯后迎面撞上瘦削、长腿、全身漆黑的菲利斯大人也就不足为奇了。他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瘦长的身体像蛛网一样堵在狭窄的通道里。
“你们这群小鬼在这里做什么?”他用同样漆黑的声音问道,掀起一股冷风,顺着楼梯从孩子们的身侧掠过。
小勇士们被粗鲁的问候吓了一跳,但很快恢复如初。佩特拉是唯一毫无惧意的人,她冷冰冰的开口道:“你在做什么?”
男人的眼睛闪了闪,戴着手套的手放到了腰间的剑柄上。“回去。”
孩子们踌躇不决,后方的几个人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但佩特拉做的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以猫咪似的速度和少女特有的轻快从黑斗篷的男人及他的匕首旁钻过,她站在那儿,挡住了他上方的楼梯。
“我们留在这儿,该回去的是你。”她简单地说。
菲利斯大人的嘴角绷紧,发出一声怒吼,他的手握住她的肩膀,粗暴地将她推下台阶。她的脚在潮湿的石头上滑倒,一条腿压在身体下方,折成了不自然的形状。接着传来一声仿佛新枝折断的脆响,以及一声微弱的呻吟,她瘫倒在石阶上,无力地滚到孩子们的面前,停在他们的脚边,几乎没有了呼吸。
他们惊呆了,年幼的班尼弯下腰,在她身边嚎啕大哭,其他人则看了一眼她折断的腿,猛地朝菲利斯大人蜂拥而上。他们幼小的喉咙发出成年人无法复刻的纯粹的嘶吼,簇拥在黑衣贵族的身边,而后者正连滚带爬地打算逃离他们。
他们将从父亲那儿带来的利刃扎进那个男人的大腿,他向前摔倒,只来得及勉强做出一次微弱的反击,一拳打在红发梅布的脸上,乱踢的腿脚也正中卡恩的脖颈。战斗的前两名伤员毫无生气地倒在了压倒性的力量下,他们身下的台阶突然变得血迹斑斑。
仿佛先前还不够认真一样,孩子们彻底地勃然大怒了,他们疯狂地殴打和戳刺倒在他们身上的人,曾经英勇的菲利斯如今只是凄惨地嚎叫着,连连求饶。终于,在最后的争斗中,帕里弯下腰,从梅布冰冷的手里取下那把鲜红的匕首,将它深深捅进了贵族的后背。
然而,菲利斯大人却顽强地坚持着,他的胳膊肘向后一拐,让莉赛尔的脑袋撞上了石墙,她的身体瘫软下去。接下来是她的双胞胎姐妹,兰温,她似乎对于莉赛尔的死亡感同身受,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任由男人手中落下的蜡烛将她点燃。她同样被一脚踢开了。
现在,除去那些堵塞了道路,血流成河的尸体以外,菲利斯大人的对手就只剩下可怜的帕里和余下的两个人了。事实证明,他的体重就是他最有力的武器,因为那些孩子都倒在了他的脚下,再也爬不起来了。如此一来就只剩下大哭着的班尼和楼梯下的佩特拉,两人都无法参加战斗。
黑衣的男人在倒下的孩子们扭曲的肢体中站稳身子,然后缓慢地朝班尼和佩特拉走去。“把刀收起来。”他说道,破损的肺脏里挤出呼哧呼哧的声音。年幼的男孩双眼充血,耳边嗡嗡作响,他被吓退了几步。而佩特拉已经无法这样做了。
“我让你们回去,你们这群小恶魔!”菲利斯大人吼叫道,他伤痕累累的脸上流下血色的泪水,“看看你们做了什么!”
班尼退得更远了,原本的呜咽变成了大声的哭泣,但是佩特拉此时拼着命站起身,腿骨绝望的断裂声也没能阻止她的冲刺,她从鲜血淋漓的牙缝中挤出这句话:“该死的邪恶。”接着将帕里的剑刃捅进了贵族的内脏。
现在,帕拉莫尔爵士终于从楼梯上冲了下来,正好看到邪恶的菲利斯大人僵硬地从胜利者佩特拉身边滚落。她站在孩子们鲜红的血海中冲他微笑,然后倒在地板上,死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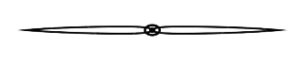
故事里丧生的孩子们与壁炉里濒死的火焰相交叠,暴风雨之夜来到了最黑暗的时刻。听众们全神贯注,他们沉浸在故事的讲述者越来越深邃的阴影中,甚至没能注意到周围的寒冷和昏暗。但身处冰凉的厨房中的霍勒斯注意到了。
于是霍勒斯不得不出门艰难地在雪地中跋涉,寻找更多的木柴。他短暂地疑惑过为什么没有客人抱怨酒馆里的冰冷和黑暗,就像过去的几天甚至几年里一样,但答案随之出现在他的脑海中:陌生人的故事在这个夜晚点燃了一团更加火热、明亮的火焰,人们因此得以取暖。
除了对凯昂国王、多索姆和菲利斯大人的诽谤以外——他已经死了吗?霍勒斯不禁怀疑,他担心故事的部分内容可能是事实——陌生人暂时还没有犯下任何罪行,甚至没有去偷面包或血汤。在霍勒斯以为客人们要逃回床上的时候,他的故事让他们留了下来,但这个陌生人有些不对劲。也许是被围裙带经年的汗水和疼痛所浸染,打从那个男人裹挟着冰雪出现在门口时,霍勒斯脖子后的头发便一根根竖了起来。现在,随着夜色的加深,随着霍勒斯听到那些将其他人束缚住的邪恶的故事,他最初的不安已经变化为确信的警惕,这个男人不仅仅是一个狡猾的骗子,他就是邪恶本身。
尽管他已经如此确定,他身上的每一根神经都在呐喊,但霍勒斯不敢现在就把陌生人赶出去,否则酒客的怒火一定会拆掉他的房子。
无论如何,在把木柴夹到惯以为常的胳膊下之后,他举起了搁置在一边木桩上的冰冷的斧头,将它一并带回。
在远处的酒馆里,陌生人的故事即将抵达那个无可避免的结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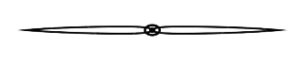
在这场针对无辜孩子们的残忍谋杀之后,又发生了许多事情:帕拉莫尔爵士对未遂的刺杀计划的震惊,彻底痛失儿女的父母们的惨叫,国王对牺牲者们颤抖着声音表示赞赏,空草席歪歪扭扭地被拖上曲折的楼梯,装满了的草席又出现在父母们的背上,军队忙着用水桶清洗塔楼,还要分出人手去保护公主的未婚夫……
在这一切结束之后,帕拉莫尔向混乱和邪恶的神祇们祈祷许久,本莎芭,希瑞克和劳薇塔,希望能得到有关这可怕的事件背后的一丝启示。当他忧虑的心灵疲惫到无法维持礼敬,而他的膝盖颤抖到无法维持直立时,帕拉莫尔爵士便把他的破法长剑普纽玛挂到床头,爬上床铺徒劳地寻求安眠。
平稳而安静地,在骑士解除武装之后,巫师多索姆突然在紧锁的房门之内出现了。
帕拉莫尔爵士一惊,从床上爬起,几乎就要说出一句赞许了。
但巫师抢先开了口,以诡秘的低音:“我知道你做的一切,怪物。”
帕拉莫尔爵士站起身,他愤怒而惊异地盯着多索姆,接着伸手去取他的破法长剑。然而他的手没来得及触及剑柄,因为就在这一刻,巫师对他施展了魔法,他的身体像冰块一样僵在原地。
看到帕拉莫尔彻底失去防御能力,多索姆发出猫一样的柔声:“这片土地上的大部分人都以为你是一位英勇的骑士,但我知道你不是。你恶毒,残忍,诡计多端,你是一个怪物。”
他的腿和胳膊无法移动了,但帕拉莫尔爵士还是找回了他的声音:“滚出去!就像我的小骑士们杀死了你的刺客那样,我也会杀死你!”
“别跟我玩这套,”黑须的巫师说,“你的剑只有握在手中时才能驱散魔法,没了它,你根本对付不了我。菲利斯和我都算不上什么刺客,你才是。”
“卫兵!救我!”帕拉莫尔冲那扇紧锁的门喊道。
“我知道你是如何策划了这场绑架案,我知道你是如何雇佣了那五个人来绑架贵族们的孩子。”巫师说。
“什么?”骑士咆哮道,他拼命控制着自己的肢体,但带来的只是双腿无力的颤抖。
外面的守卫正猛烈地敲着门,希望得到回应。
“我知道你是如何与那五个人见了面,要支付他们的报酬,”巫师继续道,“可他们得到的酬金只有你的斧头。”
“把门砸开,卫兵!”
“我知道你是如何穿上被你杀死的绑匪之一的衣服,伪装成他,并且当着孩子们的面冷酷地杀害了杰里米。我也知道在那之后,你是如何伪装成从来都和你不沾边的高贵骑士,冲进来假装救了那群孩子。”巫师说道,他的话语中第一次有了热度。
房门在守卫的撞击下开始碎裂了。
帕拉莫尔痛苦地嘶吼,“以一切神圣的名义——”
“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牵起公主的手,为了得到她,你甚至杀害了孩子们,你策划了这起绑架,同时扮演着恶棍和英雄,你以婚礼的保证作为要挟,去换取你的营救。”
帕拉莫尔爵士双腿的颤抖变得剧烈,仅仅是碰触就让整张床都震颤起来,挂在床头的长剑也一样。
“我还知道你是如何寄出这封信的,”巫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举在面前,“你寄信给菲利斯大人,请他今晚与你见面,你知道你的‘骑士’们会拦住他。”
“那根本不是我的笔迹!”帕拉莫尔喊道,他剧烈地颤抖着,叮当作响的长剑开始向他僵硬的双腿倾斜。
靴子踹门的声音愈加响亮了,木头开裂的声音不绝于耳。但随着多索姆的手势,大门上闪过一道蓝光,魔法的力量使它如钢铁般坚固。
“还有那个袋子里,”巫师知道如今自己有的是时间,于是喊道,“在那个装有五颗绑匪头颅的袋子里,也躺着杰里米的脑袋——就是你用木偶雕刻,又出现在佩特拉床头的脑袋!”
巫师向装着人头的袋子冲去,可他的手指最终没能握住它。强大的长剑普纽玛就在这一刻落下,它落到帕拉莫尔石化的腿上,驱散了上面的魔法。仅仅一次呼吸的时间之后,长剑从剑鞘里呼啸而出,砍上巫师的脖颈。
帕拉莫尔的利刃切下了宫廷巫师的头颅,也带走了大门上附加的法术。随后冲进房间的守卫们只看到一阵血雨,那颗人头因血液喷涌而出的冲击力而落到床上,多索姆的尸体则瘫倒在染红的口袋之上,已经浑身湿透了。
看到这反常的一切,守卫们冲进来,拦下了帕拉莫尔。也许是因为天色过晚,或是因为巫师离奇的言辞,或是守卫们以二敌一的威胁,总之帕拉莫尔爵士在躲避两人刀锋的同时,长剑捅进了其中一人的眼窝。伤者懦弱的同伴向后退却,在楼梯口大声发出警告;而与此同时,出于对另一个人剑伤的怜悯,帕拉莫尔将长剑彻底顶进了他的脑袋,好使他得以安息。
城堡里警报声大作,“凶手是帕拉莫尔!抓住他!杀死他!”
帕拉莫尔爵士注视着另一名逃走的守卫,跪倒在他脚下的尸体旁。他高贵的脸颊上落下一颗泪珠,心灵的眼睛凝视着自己的人生余下的这片血色的废墟。他决心记住那个毁掉这一切的人,拍了拍多索姆的头,并将其愤怒地装进自己的袋子里,发出沉闷的声音。接着他庄严地站起身,呼吸着被血液和汗水浸透的空气,大步走出了房间。他知道,即使自己逃离了命运,也会得到不公正的放逐。
那的确是他的结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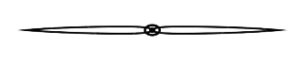
“那么,亲爱的朋友们,”身穿长袍的陌生人用左手抚摸自己的黑须,沙哑地说道,“这就是有生以来最伟大的英雄的悲剧。”
除了炉火的噼啪和狂风的呼啸,房间里一片死寂。曾经蔑视这个破落男人的人们,此时都以饱含尊敬和敬畏的目光凝视着他。并不是因为他的话语和故事,而是因为他身上某种更加基础,更加神秘,更加接近于存在本质的东西。魔力。那些曾经拒绝给予他一份餐水的人现在会非常乐意请他进他们最好的庄园里享受盛宴,他们会把丈夫和儿子交给他当士兵,会把妻子和女儿交给他取乐,他接下来的话则更加剧了他们的崇敬。
“亲爱的朋友们,这就是我之所以来到你们身边的悲剧。”甚至连风与火都安静下来,聆听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因为,你们瞧,我正是帕拉莫尔爵士。”
说着,他扔下缠在身上的湿透的破布,从那个陌生人巨大的躯体里,显露出一位年轻,优雅,强大的银眼战士。他的脸与方才与他们对话的那张干瘪、阴森的脸庞大不相同,后者——多索姆的断头——像木偶一样戴在战士的右手上,死去的巫师的嘴巴正随着战士的手指移动而移动,它们正顶在人头干枯的上颚和粗糙的舌头上,在这整个晚上,在如此漫长的叙述当中,聚集起来的村民们都在聆听这个死人的故事。
老人的声音如今从年轻人的嘴里传出,他的手指操控着下巴和舌头,“相信他,你们这些人!这是有生以来最伟大的英雄!”一块棕黑色的软泥滴在帕拉莫尔的胳膊上。
只有霍勒斯此时跌跌撞撞地走进大堂,他被这件事吓坏了;但这种腐坏丝毫没有影响到其他人。凯帕尔布里格普通的居民们离开座椅,惊叹着向高大的骑士和他恐怖的木偶走去,他们簇拥在他的身旁,就像故事里的孩子们那样,“求你教导我们,骑士啊,领导我们吧,帕拉莫尔!求你保护我们,从敌人的手中拯救我们!”呻吟和呼喊声交杂,几乎无法用人类的语言形容。
而在人们的中心,他们崇拜着的灿烂骄阳伸长他血迹斑斑的手,拥抱他们。“我当然会拯救你们,只要你们跟随我,做我的战士,做我的骑士!”
“我们甘愿为你而死!”
“让我们为你而死!”
“帕拉莫尔!帕拉莫尔!”
歌颂的声音压倒了风与火的咆哮,如果帕拉莫尔一声令下,人们高举的双手甚至可以将屋顶掀翻。
赞美是如此热烈,以至于没有人——甚至是近似于神的帕拉莫尔——注意到霍勒斯
闪着寒光的斧头,直到它使鲜红的液体从骑士的脖颈处汩汩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