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保罗 S. 肯普
翻译:青萝
在进入夺魂要隘的瞬间,达妮菲失去了杰格拉德的踪影。上一刻,他还在身边;下一刻,他已经踪迹全无。
只留她独自一人。
一条狭窄的甬道向前延伸开来,两侧是近乎垂直的石壁。一片暗淡的灰色迷雾在地板上缓缓蠕蠕。她的皮肤因为阴森的寒意而暴起了一层寒粟。
对此毫不介意,她沿着甬道向前走去,感觉自己似乎每走出一步都跨越了几里格,每呼吸一次都花掉了几天时间。她加紧步伐,等待着夺魂者的出现。
仅仅片刻之后,沙沙的低鸣声在她脑海中响起,然后又变成了嘶嘶的嘘声,痛苦的悲鸣。她找不到声音的源头。
她寒毛倒竖,呼吸急促。
它就在她的身后!她完全确信。
她放低流星锤,慢慢的转过身来。
就在五步开外的地方,夺魂者蜿蜒曲折的朦胧躯体填满了整个隧道。在它那空洞目光的凝注下,她显得如此卑微渺小。大张的血盆大口能够轻而易举的吞下一头食人魔,在它的喉咙深处,在它的内脏中,有数不清的灵魂熠熠闪光,看上去就像孩子们的玩具娃娃一样细小无助,就像拷问官(torturemaster)手下的牺牲品一样绝望痛苦。
达妮菲挣扎着重拾自我,尽量不表现出任何恐惧。她知道自己正面对着自身信仰的另一次试炼。她紧按着自己的圣徽,掌心的琥珀一片冰冷。
夺魂者是如此巨大,如此古老,如此恐怖…………
灵魂的哀鸣声充斥着她的脑海。她咬牙强忍着,尽管她恨不得钻开自己的头骨。
夺魂者大大的张开巨口,同时引诱并挑逗着她走上前来,以便用它将要向她展示的东西来试炼她。她移动仿佛灌铅一般沉重的双腿向前走去,但是仅仅走了两步就停了下来。
达妮菲以手势示意它到自己这里来,同时用自己最为诱惑娇媚的声音柔声低语道:“你来我这里。”
它毫不迟疑。嘴巴大张着,它向她冲来,速度快的令人恐惧。
她静立原地,一直到它的喉咙把她完全吞没。
一千个低沉的喃喃自语,恐怖的,无望的声音——被束缚的灵魂的声音——在她的耳中回荡起来,响彻了她的生命本质。
她报之以一声自己的尖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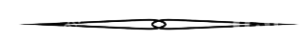
当索拉林家族的军队变幻队形,为下一次进攻做着准备的时候,艾妮瓦尔,阿格拉契·狄尔家族主母的长女,站在高高的城墙上观察着下面的战场。她几乎什么也看不到,出于战略需要所施放的黑暗结界遮盖了大部分军队的调动。大声的命令声和金属的撞击声不时飘过护城壕沟。
在她身边,乌尔甘(Urgan),阿格拉契·狄尔家族的脸上带有伤痕的武技长,说到:“他们将会在一个小时之内发动进攻,艾妮瓦尔女士。”
艾妮瓦尔点点头。她用双手按住挂在腰带上的两柄轻型附魔钉头锤的手柄,每一把的锤头都雕刻成了一只蜘蛛的形状。
“这在时间上绝不是巧合。”她沉声说到,不过没有解释。她假定这场进攻是设计来保护首席大法师的。他的同盟者当然会知道主母大人已经认识到他的诡计。
艾妮瓦尔来回打量着由精金和巨石垒起的高墙。它们已经矗立了几千年,只是不知道这一次它们会不会就此倾覆?
狄尔家族的战士们沿着雉堞一字排开,艾妮瓦尔从他们僵硬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们都感到了即将来临的进攻。一阵紧张的沙沙声在队伍中蔓延。
“我们会坚守住。”艾妮瓦尔说到,即是对自己也是对乌尔甘。
武技长回应道:“我们会的。”
艾妮瓦尔认为她在乌尔甘的声音中听到了疑虑之意,但是她决定忽略掉。她怀疑自己到底是希望她的母亲能够成功阻止首席大法师,还是希望她失败。如果主母死去,并且卓尔巫妖的命匣被摧毁,那么艾妮瓦尔也许——也许——可以通过谈判来结束这场围攻。
但是首先,她需要坚守住城墙,在她的两只弗洛魔,或者她的家族法师不在的情况下。索拉林家族的战争号角响了起来。
“他们来了。”乌尔甘说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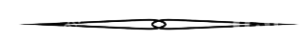
蜘蛛魔像每一根前肢的末端都是一只锋利尖锐的黑玉脚爪,长度和一把短剑相当,不断蠕动的下颚中长满了和贡夫手臂一样长的毒牙。
贡夫对此毫不在意。被法术的力量转化成为一名技巧高超的战士,他径直冲到魔像面前,双手高举着战斧。
魔像蹲伏在他前进的道路上,在贡夫进入它的攻击范围之前,快速的挥舞着两只利爪。
预见到它的动作,贡夫旋身避往一侧,同时用手中的战斧挡住了其中的一次重击。魔像的另一只脚爪挥向一个镜像,一击即中,令它砰的一声消失不见了。
利用旋转的力量增加自己的冲力,贡夫疾速靠近,用灰矮人战斧大力劈砍,从构装体的胸腔上劈下了一大片黑玉。利用法术所提高的速度,他紧随另一条须肢揉身而上,在魔像的一条腿上劈斩出一条深深的裂痕。
蜘蛛向后跳去——它的重量压碎了一张长椅——同时用一只爪子猛击向贡夫,然后是另一只。贡夫俯身躲避, 避开了这次进攻,同时再次试图靠近。又有两个幻象消失了。构装体以令人惊骇的速度飞快移动着,仿佛完全无视自身的重量。
有那么一段时间,双方在仅仅距离几步之处盘旋对峙着。魔像跨过长椅,在移动的过程中压碎了不少石头,同时犹如催眠一般挥舞着它的须肢。每前进一步,它的脚爪都深深的插入到地板中。
贡夫的目光紧紧的追随着它,脚步机警的移动着。
神殿大门处传来的隆隆声令贡夫转头看去。有人正在试图穿过他的封锁法术。雅丝瑞娜已经找到他了。 见到他分心,魔像立刻向他猛冲过来,一路上打翻了无数长椅。贡夫就地翻滚,俯冲到了另一边。数只利爪齐齐的插入他身侧的地板中——先是一只,然后是另一只,接着是第三只——又是三个幻象迅速的接连消失。魔像的一只爪子割伤了他的肩膀,顿时鲜血淋漓。他的戒指马上开始治疗这个伤口。
贡夫一跃而起,用战斧中途截住了一次斩首攻击,同时顺势斩断了魔像的一条长腿,一截有食人魔手臂那么大的黑玉轰然插进了附近的一张长椅中。
大门处又传来另一阵隆隆声。他的法术再一次发挥作用,但是贡夫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避开了一次挥击,然后是另一次,他飞奔冲进魔像的怀抱,同时用战斧猛砍它的头部。他从魔像的头上斩下了一条长长的黑玉,但是对方迅速后退,压倒了一片长椅。贡夫奋力前冲,然而这个生物突然对着他喷出了一团黑雾。
酸雾,贡夫辨认出了黑雾的种类,但却无法躲避。个人结界虽然可以保护他自己的肉体,但却无法保护莱瑞凯尔的身体。他的皮肤感觉到了一阵如同燃烧般的剧痛,没有经过附魔的外衣被酸雾溶解掉了——谢天谢地, 这其中并不包括他用来携带精华法术材料的附魔长袍——当酸雾使得皮肤片片脱落的时候,他裸露在外的肌肤全被灼伤了,到处都是水泡。地面上的石板和周围的排排长椅青烟袅袅,被腐蚀得坑坑洼洼。即使酸雾已经消失,空气中仍然充满了刺鼻的味道。
贡夫咬紧牙关,强忍疼痛,跳过一张被酸液蚀平的长椅,从魔像身上砍下了一条长腿。然后是另一条。魔像报之以一阵狂乱的爪击,迫使贡夫向后退去,同时消灭了他的所有幻象。
鲜血和汗水不断的从贡夫的皮肤上滴落下来。他的呼吸变的急促沉重。疼痛使得他的速度慢了下来。如果这个魔像与它的同类一样的话,他知道它很快就可以再次使用酸液喷吐了。只要它在自己的附魔身体内部再次积聚起足够的腐蚀性物质。首席大法师怀疑自己能否在另一次喷吐中幸存下来,因此贡夫必须抢先摧毁它。
他躲过了另一次爪击,向后举起战斧,然后——
一次猝不及防的重击命中了他的胸膛。幸亏力场盾牌和法术盔甲的保护才让他没有被一劈为二。然而,这次打击的力量仍然让他摇摇摆摆的向后退去。他跌跌撞撞,胡乱的挥动着战斧,最后被一张残破的长椅绊倒, 仰面摔在地上。
蜘蛛向他俯身冲来。碾碎了破损的长椅。它的下颚大张着,须肢向他直刺而来。贡夫狂暴的旋舞着战斧, 翻滚着,试图重新站起来。魔像的一只利爪自上而下直取他的咽喉,但是力场盾反转了这次攻击,不过残余的冲力还是把他再一次打倒在地。
他站起身来,挥舞战斧保护着自己,向后疾撤。魔像奋力急追,当距离缩短到足够近之后,猛的张开下颚咬去。这次啮咬拉住了贡夫的斗篷,扯得他失去了平衡。接下来的一次爪击打得他一下子趴在了地上,战斧几乎脱手而出。
贡夫狂怒的暴跳而起,回手反击魔像的头部,正好击中它的眼簇上面。黑玉碎屑四散飞溅,魔像被迫向后退去,须肢恐吓般的挥舞着。贡夫站稳脚跟,也稍微向后退了一点。
呼吸浊重,贡夫知道自己不能浪费时间了。
很快的,魔像就能够再次使用它的酸液喷吐了。
很快的,雅丝瑞娜和她的法师们就能进入神殿了。
主控结界的脉络就像某种奇形怪状的藤蔓一样从蜘蛛魔像的腹部伸了出来。贡夫知道,在结界的末端,魔像的体内,就是命匣。他必须加快进攻。
他一边挥舞战斧保护着自己,一边向祭坛方向后退。蜘蛛魔像紧随而上,飞快的爬过一排排被酸雾腐蚀得伤痕累累的破碎长椅。
贡夫假装一个踉跄,上当的蜘蛛立刻猛扑过来。首席大法师向一边俯冲躲避,然后迅即重新站起,同时狠狠的向下斩击,从蜘蛛魔像的肩膀上砍掉了它的一条长腿。
魔像用另一条长腿击向贡夫,同时设法把头转向他的方向——这次攻击在贡夫的大腿上划开了一条长长的口子——但是贡夫跳到了它剩下的两条长腿之间,挥舞着战斧狂暴的猛力劈砍着。大块的碎片飞散到空中,魔像竭力试图转过身来。
魔像的又一次挥击打中了贡夫,肋骨破裂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他的呼吸几乎中断了,但是他不敢停止攻击。他的脚踝被魔像狠狠的咬住了。
视野中绽出点点金星。剧痛沿着大腿一直蔓延上来。然而贡夫呐喊着继续进攻。他的战斧高低起落,上下翻飞。大片大片的魔像碎片四散飞溅到神殿中,活像黑湖上漂流的残骸。
经过了一段时间长短不太确定的迅猛进攻后,贡夫开始意识到蜘蛛魔像已经不再移动了。在法术诱导的狂暴心态下,他又猛砍了魔像好几次,这才心满意足的停下手来。
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疼痛几乎使他失去了知觉。大半个魔像就躺在他的面前,四分五裂,破损不堪。它的主体压住了他的大腿。魔像碎片散落的到处都是,分散在破损的长椅之间。
神殿的双重大门处又传来了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几乎让整座建筑都为之震颤。雅丝瑞娜和她的家族法师们仍然没能打破贡夫的封门法术。接下来她们会尝试从窗子进入。
咝咝的抽痛着,他用灰矮人战斧撬开魔像的身体,把自己的脚轻轻抽了出来。骨头摩擦着骨头,剧痛几乎令贡夫把他之前在办公室中吃下的蘑菇都吐了出来。他转头不去看碎裂的脚踝。
他的戒指开始治疗伤口,但是恢复的速度太慢了。他把手伸进长袍——长袍上的魔法使之免于被魔像的酸性喷吐溶解——取出了两瓶治疗药水,这本来是做为法术材料而准备的。他用牙齿撕掉了瓶口的封条,慢慢的啜饮着瓶内温暖的液体,一瓶接一瓶的。
他的脚踝再度结合,大腿和肩膀上深深的伤口也愈合了。甚至连大部分酸雾烧伤也被治愈了。
他叹了口气,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脚踝,发现它已经完好如初,于是便爬上了魔像的身体。在这里,他找准立足之处,跨坐在主控结界消失在魔像躯体中的那一点。他高举战斧,开始用力削砍。
随着每一次挥动手臂,他变的越来越迫不及待,在他的视域中,来自命匣咒文的光芒变的越来越辉煌明亮。
在大约劈砍了十次之后,战斧在蜘蛛魔像的胸腔上开出了一个空洞。贡夫停了下来,汗水涔涔,瞪大眼睛向里看去。
在里面,飘浮在半空中,被主控结界的脉络所缠绕的,是一个微光闪闪,拳头大小的红色球体。在他的注视下,球体变成了黄色,然后是绿色,再然后是紫罗兰色。
贡夫观察到这个球体循环经历了七种颜色,然后又重新开始新的一次循环序列。隐约的,他知道这个球体是什么——这是一个虹光法球(prismaticsphere)。各种颜色彼此嵌套,各色球体交替出现,就像幽暗地域中一种蕈类植物的层瓣一样。卓尔巫妖必然找到了一种方法,令这个虹光法球永存不衰。他把他的命匣置于其 中,然后又把它们全部放在一只特别制造的魔像之中。
贡夫知道如何解除虹光法球。特定的法术可以抵消特定的颜色。如果不解除魔法就触碰某种颜色的话,只会造成伤害甚至是死亡。只有在解除掉所有的颜色之后,他才能取出隐藏其中的命匣。
这需要花费时间。而他几乎没有时间了。除此之外,他还有另一个难题。
把他变为战士的变形术临时改造了他的思想,关闭了他脑海中通往魔网的大门。他知道自己能够施法,但是允许他与魔网连接在一起的知识却已经不翼而飞,暂时被变形法术授予他的关于战士的知识排挤得一干二 净。
他无法提早结束法术,必须等到法术自己完成全部过程。只有在此之后,他才能着手解除眼前的虹光法球。
在他头上,一部分挡在神殿窗前的石墙开始簌簌碎裂,被雅丝瑞娜的法师所施展的某种法术所破坏。碎石如雨点般掉落在神殿的地板上。
在贡夫和狄尔家族的军队之间,如今只余一堵力墙。他几乎没有时间了。
一阵簌簌的摸索声令他转头看去。眼前所见的一切令他的胃部一阵翻涌。
他从魔像上面砍下来的每一块碎片——长腿,大块的胸腔,爪子,以及腹部的碎片——正在噼啪作响的裂开条条裂纹,八条黑玉长腿从裂缝中伸展出来。被贡夫劈落于地的不少于六十块的魔像碎块已经象萌芽一样,重新复活形成了新的魔像。战斗还未结束。
一小时之内的第十次,贡夫恶狠狠的诅咒起卓尔巫妖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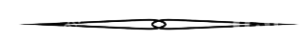
在布里尔林区(Braeryn)的阁楼上,达妮菲透过没有玻璃的狭小窗户向外看去。纳邦德尔时柱的三分之二散发着红光。今日天色已晚。
达妮菲已经失去了时间的概念。对于她来说,每一天都是那么的相似,每一个小时都毫无区别的通往下一小时。
她发现不依靠纳邦德尔时柱,而是依靠尸体来计量时间更容易一些。自从罗丝选择了她——达妮菲甚至不想提起她的名字——做为 Yor’thae 之后,已经有三十七具尸体了。
尽管在罗丝选择她的 Yor’thae 之前,达妮菲从未来过魔索布莱城,但是从那之后,她已经开始认识这个城市,并且开始憎恨它了。
在她的右边,远远的越过魔索布莱城的巨洞,达妮菲注视着通往提尔·布里契(TierBreche)的巨大阶梯。即使相隔如此之远,她仍能看到它,这完全是因为它那庞大的体积和点亮在步阶上的紫罗兰色妖火。在阶梯尽头的高原上——在这个距离上她无法看到——矗立着罗丝最为辉煌壮丽的神殿,蜘蛛教院,蜘蛛神后信仰的心脏。达妮菲从未能够置足其中,而且也永远不会有这个机会了。
蜘蛛教院被那条母狗所把持,罗丝的 Yor’thae。
愤怒仍然在煎熬着达妮菲,对于 Yor’thae 的永无止境的憎恨,令她迁怒于所有来到她这里的男性。达妮菲为罗丝创造了她自己的神殿,她自己的蜘蛛教院:一座深藏在布里尔林区中的极端狭小简陋的阁楼。在这里,她编织着自己的蛛网,并以罗丝之名进行猎食。
她从窗子探出身去——她的圣徽仍然挂在颈子上,不住的摇摆,只是琥珀上蒙上了一层油脂和烟灰——看向下面的街道。醉醺醺的瘾君子们象眼窝深陷,茫然无措的幽灵一般在深巷中神出鬼没。同道的娼妓们在她楼下的门洞中徘徊,向经过身边的任何人和任何东西卑微的恳求着。
成群结队污秽的兽人和熊地精向这些堕落的卓尔女性送去秋波。达妮菲可以看出这些娼妓已经把她们的尊严和肉体一起出卖掉了。但她绝不会如此,她仍然在侍奉蜘蛛神后,而且将会一直到永远,无论她是不是Yor’thae。
街道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下水道中的淤泥和垃圾。“臭街(TheStenchstreets)”,它们被如此称呼,非常公正。达妮菲只能认为整个布里尔林区都是一座露天的下水道,她无处可逃。
她不会让达妮菲逃走。
刚倒尽的夜壶的气味传进了窗户,令达妮菲不禁皱紧了鼻子。在她被损伤的右侧脸颊处,数道僵硬的伤痕使得她的表情呆板笨拙。想到自己被毁坏的容貌,她忍不住又是一阵难以遏制的怒意。她希望自己的憎恨能够飘过空气,穿越巨洞,一直抵达提尔·布里契。
从很久以前,她就放弃隐藏自己的伤痕了。它们是她的一部分,就如同她的信仰那样真切,就如同她的憎恨那样鲜明。
在罗丝做出她的选择之后,蜘蛛神后完成了她的复苏,而 Yor’thae 则耀武扬威的返回了魔索布莱城。她允诺引导蜘蛛神后和她的追随者们进入一个新的纪元。
但不是她的所有追随者。
Yor’thae 为了达妮菲的放肆而惩罚了她,强迫她过一种无家可归的生活,剥夺了她的几乎所有财产,毁损了她的容貌,令她变的丑陋不堪,甚至拒绝赐予她一个尊严的死亡。
甚至就连罗丝本人似乎也抛弃了达妮菲。
女神不再赐予这个前战俘法术,反而只在她的梦中出没,尽情的折磨她。每当她入梦之后,达妮菲就会看到八只蜘蛛的幻影,八组毒牙,长腿,眼睛,以及毒素。
尽管如此,但是达妮菲拒绝贴上背教者的标签。她仍然虔心敬奉罗丝,尽管她的集会上永远只有一人。贫穷而丑陋,她被迫向男性出卖肉体以求温饱。尽管 Yor’thae 损毁了她一侧的面容,男性们却仍然渴求着她娇媚的肉体,愿意为此付出金钱。达妮菲憎恨他们的抚触,轻视他们自以为她已经向他们屈服的幻想,但是无论如何她必须生存下去——象任何最好的蜘蛛一样。
当 Yor’thae 把达妮菲推入贫穷污秽之中的时候,她曾经放声大笑,认为这种贫困交加的生活将会使达妮菲软弱。但是就像所有的蜘蛛一样,达妮菲是一个幸存者,眼前的困苦对于她来说,只是一长串考验中的一个而已。她已经并且将会战胜它。她将会变的更强大。她不会被打败,永远不会。
如果说达妮菲曾经从罗丝的信仰,从她做为赫莉丝卓·莫兰的奴隶的生涯中学会了一个信条的话,那就是生存就是一场考验,永恒的考验。强者捕食弱者,而弱者只能承受和死亡。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尽管达妮菲并非 Yor’thae,但是她拒绝成为弱者。
她离开窗边,转过身,看向布置简陋的阁楼。她更喜欢把这里想象为她的蛛网,一张谦逊的蛛网,就像黑寡妇的蛛网一样,网中潜伏着一只残酷的掠食者。
在附近的墙边,一张蘑菇纤维编织成的草铺靠墙摆放着,上面铺着肮脏的毯子。每天,她都会带着被单来到黑湖岸边洗涤——这件例行公事般的清洗工作很早以前就已经成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信仰仪式——但是汗水和性爱的气味始终荡涤不去。一直以来,她始终睡在地板上,拒绝在她曾和一名男性共同分享过的床铺上休息。一盏黏土油灯摆放在床头的凳子上,微小的火焰在污浊的空气中忽明忽暗。角落里摆放着一把石椅,她在上面挂了几件她自己的衣服。对面的墙角则摆放着一把夜壶和一个脸盆。
除了自己的信仰,圣徽,以及藏在腰带上的一个小瓶中的黑根精华(the blackroot distillate)之外,达妮菲一无所有。每隔四个十日,达妮菲通过向一名在市场区外面工作的年老的半卓尔药剂师出卖肉体,来重新填满这个小瓶。很早以前,她就通过慢慢的曝光,使自己免疫于这种毒药。
她堕落的很远,她清楚这一点,甚至比当初她成为战俘的时候还要远的多。但是她拒绝放弃信仰。大部分人相信她不过是一个精神错乱的娼妇,或者是一名满脑子荒谬妄想的被遗弃的巫婆。但是她不是,她是一只蜘蛛,她正在接收试炼,仅此而已。
她在深坑魔网中没能通过罗丝的试炼——这就是为什么她没有获选成为 Yor’thae——但是她将会弥补这次失败,总有一天她会重获蜘蛛神后八只眼睛的宠爱。
在此期间,达妮菲以罗丝之名进行谋杀。每隔八个来到她阁楼上的客人都成为了她的猎物。也许蜘蛛神后不回应达妮菲的祈祷,但是达妮菲仍然不间断的向她进行献祭。
她把尸体卖给一名年老的卓尔蘑菇农场主,以此毁尸灭迹。达妮菲的牺牲者最后全都变成了东尼加顿湖区蘑菇田里的肥料。
弱者被强者捕食,她想到,同时在伤痕下面笑了起来。门上传来的敲击声令她转过身来。
“菲(Fae),”一个含混不清的声音在门后响起。“打开门,我想要和你共享欢乐。”
达妮菲知道这个声音。海根(Heegan),一个失败商人的次子,他经常沉浸在蘑菇酒和葡萄酒中,搞得自己烂醉如泥。
“稍等一下。”达妮菲大声回答道,这名男性照做了。海根就是第八个。
达妮菲把装着黑根精华的小瓶从钱袋中取出来,涂抹着她的手指,然后又在嘴唇上抹上了一层,然后摆出一副笑容,走到门前,打开了房门。
走廊上站着的正是海根,他的白发乱糟糟的,肮脏的衬衫上有几颗纽扣没有扣上。达妮菲比这名男性高大约两掌。她看着他湿润的红色眼睛,想到——你就是一个弱者。
“很高兴见到你,‘菲’,”他醉醺醺的说到,挑逗的看着她高耸的胸膛,她只穿着一件破旧的衬衫。“我们真是不错的一对,是不是?”
他在她的面前摇晃着一袋硬币。
达妮菲抢过硬币,同时一掌重重的打在他的脸上。他捂着流血的嘴唇笑了起来,抓住她的手臂,把自己的嘴唇重重的压在她的双唇之上。他的呼吸污秽,而他兴奋的轻哼声甚至更糟。她咬牙忍受着,知道随着每一次亲吻,他都更进一步的深陷入她的罗网。
她允许他引导着自己来到床边。他试图把她推倒,但是她利用自己更胜一筹的力量反身压倒他,强迫他倒在床上。他醉醺醺的露齿而笑,胡乱咕哝着一些荒谬可笑的爱慕之词。
她跨骑在他的身上,而他兴奋的轻舔着嘴唇。他的双手摸索着她的衬衫,她的腰带;从他的动作中,她可以分辨出过多的葡萄酒已经令他的思想云山雾罩了。他的手掌掠过装有黑根精华的小瓶,完全没有停留,他是如此急切的想要触摸她的肌肤。
笑容涌到他的脸上,她一边戏弄着他,一边默数着另外三十下——直到他热切的表情变成困惑,然后又转为惊慌失措。
“我怎么了?”他问道,他的嗓音迟钝而脆弱。“你对我做了什么,你这条母狗?”
他试图把她从身上推开,但是麻药已经生效。他失去了力气,他只能笨拙的试图抓住她的肩头。片刻之后,他被充分麻痹了,只能恐惧的瞪视着她。
她冷酷的注视着他,仍在娇媚的微笑,同时开始她的咒语。她的声音呼唤着罗丝,以这名男性的死亡令她愉悦。当她结束祈祷之后,她用双手圈住他的脖子,扼死了他。
他的眼睛凸起,咯咯的挣扎着,然后就死去了。
“你是弱者。”她俯身在他耳边柔声低语。“而我是蜘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