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菲利普·阿桑斯
翻译:锅子、塞巴斯汀、姽婳深闺、诺伯、Evenlong、Rainagel
校对:塞巴斯汀、微睡、Evenlong、Rainagel、Pksunking
地表城市提凡顿的废墟之下一英里半深处的地底世界中,两个卓尔一路疾奔。
达妮菲喘着粗气,尽量跟上瓦拉斯的步子,但她也只能勉强跟在他身后几步之外。这个斥候以一种介于跑和走之间的方式移动,他的双脚有时候似乎根本就没有接触到隧道底部光滑的石头。飞快地穿过一堆让人晕头转向的门之后,瓦拉斯告诉她到辛迪尔林的路他们已经走了一半多,而且这仅是他们一天内行走的路程。
达妮菲钦佩这个斥候在幽暗地域探路的能力,她甚至都要不去计较他那明显地缺乏野心和动力了。斥候仿佛对现在他所扮演的这种被雇佣的角色——一个为昆舍尔·班瑞效力的斥候或小厮——感到很满意,这种想法与这种心满意足对达妮菲来说是完全陌生的。
毕竟,她最后及时想到,瓦拉斯不过是个男性罢了。
斥候突然停住脚步。这让达妮菲为了不撞在他身上,不得不有失体面地踉跄了几步才停了下来。但是她还是很高兴能停下来休息一会,所以也就没有抱怨。
“怎么——?”她问道,但是瓦拉斯抬起手示意她保持安静。
尽管身为一个战俘,充当又蠢又笨的赫莉丝卓·莫兰的仆人已经这么多年,达妮菲依然无法习惯被人命令闭嘴。斥候那轻蔑的手势让她怒气冲天,然而她很快冷静下来。瓦拉斯在履行他的职责,如果他要求沉默,那么这时出声就很可能会送了他们俩的小命。
瓦拉斯转向达妮菲。纵然她刚才的话仍然隐隐地回响在地底冰冷而静止的空气中,但让她惊奇的是,他的脸上连一点厌恶和恼怒的神色的都没有。
另一道传送门就在前面。他用手语告诉达妮菲。它能缩短我们的路程,差不多能抵达辛迪尔林的东大门。但它不是我惯常用的那个。
你以前用过这个门,不是吗?她同样用寂语回答。
传送门,特别是这样的传送门,瓦拉斯解释道,就像一个漩涡。它们都相当引人注意。
你指的是?她问道。
达妮菲灵敏的听力没有听到任何声响,她那同样出色的嗅觉也没察觉除了她和斥候以外的任何其他的味道。但这不表示这里只有他们两个人。
仿佛是读到了她的想法,瓦拉斯回答道,在幽暗地域你永远不会是独自一人。
这到底是什么?她问道。我们能避开吗?或者杀了它?
也许什么都没有。他回答道。也许吧。我希望如此。
达妮菲冲他笑了笑。瓦拉斯把头转向另一边,这个笑容让他感到惊讶和迷惑不解。呆在这,他用手势说道,别动。我到前面去看看。
达妮菲向后面看了看他们走过的道路,然后又转过头盯着如今前进的方向。这条隧道大概有二十五到三十尺宽,高度和宽度差不多,前后两端都伸向无边无际的黑暗。
如果你敢把我一个人丢下……达妮菲用她的手指和那双冷酷无情的眼睛无声的威胁道。
瓦拉斯对此毫无回应。他似乎只是等着她说完。
达妮菲重新扫了前方这个似乎无穷无尽的隧道一眼。只半个心跳的时间,当她转回头来, 瓦拉斯已经不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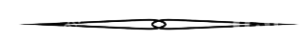
瑞厄德慢慢打磨着分裂者锐利的锋刃。这魔法剑几乎不需要打磨,然而这种机械的简单杂务更能让他静下心来思考。这把剑的外表上并没有拥有智能的迹象,但瑞厄德多年以来一直相信分裂者在享受他给予它的关怀。
他独自坐在与赫莉丝卓共享的那间摇摇欲坠、杂草丛生的茅屋里。森林的气息萦绕在他身周,挥之不去,大有连他与他的剑独处的思考时间都一并侵略之势。在地表这无尽的天宇之下的白昼中,他现在已经算是很自在了——即使赫莉丝卓没在他身边。
格斗武塔的教官独自一人是因为赫莉丝卓所加入的那个圈子没邀请他一起加入。那些古怪的地表卓尔异教徒们在计划着什么事情,显然赫莉丝卓和她新发现的玩具——新月之刃——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他是杀死了那只袭击他的暴怒的野兽,可尽管菲丽安向他解释过多次,他依旧不明白这怎么就能成为他被置之圈外的原因。但瑞厄德明白的是,不止这一个原因令他被排除在外。
他一个人呆着是因为不像赫莉丝卓;他既没有公然背弃蛛后,也没有公开投向她这阳光之下的对手——舞蹈少女——的怀抱。瑞厄德没法理解他们这不着调的女神。舞蹈少女?他们就把他们的生命浪费在追随舞蹈之道上?这实在是太扯了,一个女神能从舞蹈这么没意义的玩意上汲取——更别提给予——什么样的力量?罗丝是个残酷而又反复无常的女神,她的女祭司们牢牢掌握着她的力量,但她是蛛后,而蜘蛛是强壮而足智多谋的掠食者——与幸存者。瑞厄德也该把自己看成是一只蜘蛛;蜘蛛从不宽恕,也从不求饶。它们织网,捕猎,生生不息。蜘蛛是有蕴意的,它们代表着力量,而力量则是任何一个卓尔所追求的。
显然不是每个卓尔。
关于为什么当女性们在密谋和策划的时候,他却在这里磨剑,瑞厄德清楚还有第三个原因:那恰恰就是因为他不是女性。在魔索布莱,瑞厄德·阿吉斯是个声名显赫的战士,有着强大的盟友并且很为他的上司们所倚重。他的日子过得很舒服,用的是有着强大附魔的武器——巨剑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他甚至得到信任,被选为那个至关重要的探险队的成员, 去寻找他们沉寂的女神。尽管如此,瑞厄德依旧是名男性。因此他必定永远屈居第二——他很清楚,可能还远不止这样。他能统领其他男性,其他战士们,但他永远不能号令一个女性。她们询问,有时甚至采纳他的意见,但他永远当不上决策者。他是一名战士——一件工具, 一把武器——但他永远当不上领导者。在魔索布莱那罗丝的女儿们中办不到,在地表那舞蹈少女的女祭司们中也同样办不到。
三条被排除在外的原因,瑞厄德思索着,在家的时候他所要面对的只有第三条而已。三条回家、回魔索布莱去的理由。
留下来的理由只有一条。
独处的时候瑞厄德常常考虑起重返幽暗地域。费瑞恩和其他人想必已经走了,继续他们的探索,就好象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了跟他们一起从蜘蛛之城出发的那个格斗武塔教官。至于他对于昆舍尔·班瑞这样的人的价值所在,瑞厄德不抱半点幻想,而费瑞恩曾经的行为也证实了瑞厄德的命比不上他的利益重要,更不用提他的安康了。
无论如何,费瑞恩的行为都是有序可寻的。瑞厄德了解这个法师,清楚在他身上能指望的是什么——哪怕那能预见的东西就是背叛。费瑞恩这个黑暗精灵不但适应了他们的卓尔本性,甚至沉醉其中。昆舍尔·班瑞也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那么厌憎彼此。这两个和其他人——甚至斥候瓦拉斯·修恩——都像蜘蛛:可预见的、能干的幸存者。瑞厄德也用同一标准衡量自身,而且和貌合神离的同伴们一起行动这件事又让他无法抗拒。
直到他想起赫莉丝卓。
在魔索布莱的那些年,瑞厄德身边不乏女性,但同蜘蛛之城其他所有男性一样,他很清楚不能陷得太深。他一次又一次认识到,他是个玩偶,是件工具,是调情的搭档,是逢场作戏的对象——但从来不是爱人,同伴,朋友,丈夫,不是地表精灵们这些古怪的称谓中的任何一种。直到赫莉丝卓出现前,这些词原本对他也毫无意义。
瑞厄德怎么也不明白,莫兰家的长女是怎么紧紧抓住了他的心的。为了能切断她施加在他身上的让他追随她的魔法,瑞厄德不惜用上分裂者独特的能力——但这不是魔法。她没念咒语,没唱圣歌,没下迷药就能让她的身影在他心头萦绕不去。她没有。瑞厄德沉思道。她所做的,所说的并没有什么特殊,尽管在以前那一打以上的占有过他的女性也说着同样的话——以嘲弄、甚至是冷酷的语调说出这带有强烈讽刺意味的话语。
赫莉丝卓只是对他微笑,引得他们的视线彼此交汇,抚摩他,吻他,畏惧地望着他,热切地望着他,懊悔地望着他,痛苦地望着他,愤怒地望着他,绝望地望着他……她诚实地看着他。瑞厄德从没见过这一切,从没在哪张属于黑暗精灵的乌木色的脸上看到过这样的表情, 从没在幽暗地域阴冷的深黑中见到过这样的景象。当她接近的时候他能感觉到她的存在,就仿佛她身上散发出某种能被他所感触到的涟漪。她只是赫莉丝卓,武技塔教官惊愕地发现, 这就足够了。她的存在完全就是为了将他从他原来的,并本将继续下去生活中拯救出来,这就是一个卓尔男性所期盼的救赎。
然而如今他在忍受同样的遭遇,在这里男性依然屈居次位,平等照旧虚无缥缈。
关于今天,以及之前的许多天他被一个人丢在一边的第四个理由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他只让它在心头闪了一闪。
他们打算杀了她。一股恶寒刷地滑过他的脊背,原本缓慢而细致地打磨着剑锋的握着磨刀石的手猛然停住。他们打算杀了罗丝。
瑞厄德闭上眼睛,长出了一口气,好让自己突然砰砰乱跳的心脏重新镇定下来。
说到底,这就是为什么赫莉丝卓被选中去找回新月之刃。这就是为什么伊莉丝翠的女祭司们肯容忍格斗武塔教官的存在——全是出于赫莉丝卓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赫莉丝卓留了下来,并找回他以前不曾见过的自信和沉着……好吧,自从他们从崩塌了的契德纳萨逃出来起就没见过。这就是为什么赫莉丝卓不再恐惧地颤抖;这就是为什么她能在晨光下醒来,在日光中呼吸。
以伊莉丝翠之名,赫莉丝卓·莫兰要前去杀死那沉睡于深坑魔网中的蛛后。瑞厄德继续磨起了剑,笑了。
也许,他想,她比她愿意承认的更像一只蜘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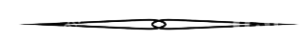
尼摩·茵菲瑞泽尔俯瞰着下方那灰矮人与蜘蛛的激烈战斗。骑着巨大的蜘蛛的卓尔战士们加入了战局——他们统统是男性。蜘蛛在他们周围横冲直撞,而骑手们却稳如泰山。这些卓尔们手持长矛——不但灰矮人们不熟悉这种武器,长武器在整个幽暗地域里都相当罕见—— 灰矮人们还没等畅饮到黑暗精灵的鲜血,就被一个接一个地穿了透心凉。
比起正继续围攻着慢慢崩溃的魔索布莱城的灰矮人来,蜘蛛骑兵的人数少得可怜。有机会亲眼目睹这些卓尔战斗的景象,尼摩很乐意浪费掉几个灰矮人炮灰。他得承认,他们表现出色。蜘蛛与长矛造成的伤亡数目不相上下,而这些骑兵身下的蜘蛛们从没失去过控制。总而言之,这是一场瑰丽的血腥之舞。
蜘蛛骑兵的中心是个身着最上乘秘银铠甲的男性,他的铠甲上明显闪烁着附魔的光芒。同其他人一样,他也手持长矛,然而他并未用长矛进行攻击。他把它高高举起,长矛上那面细长的令旗在幽暗地域清冷的空气中飘扬。思索片刻,尼摩认出了令旗上的徽记。这些骑兵属于香巴拉家族——一个效忠于班瑞家的次阶贵族家族,以其训练有素的骑兵享誉整个幽暗地域。执旗的黑暗精灵想必就是骑兵们的队长。
一个骑兵一枪捅穿了两个灰矮人,借着他们的重量又把另三个灰矮人抡倒在地,这情景让尼摩不禁粲然。
当第三次获悉这里异常活动之后,他来到了这条特殊的隧道。一天前灰矮人们刚刚干掉了一个魔索布莱的斥候,不过他们也确认了原来那里还有其他的卓尔,现在统统逃跑了。这不是防守最严密的通道,魔索布莱肯定会检查这里,因此尼摩一直密切注意着这条隧道。
干掉斥候后,尼摩就让霍加王子往这边增兵,希望灰矮人的数目既足够缠住卓尔们,又不至于多到就此封锁这条通道,他意在引蛇出洞,而那些傲慢自大的贵族也必定会就此上钩。
尼摩在隐身术的掩护下倒挂着,他的魔斗篷上的附魔能防止其他人通过类似的法术找到他,万一敌人真抬头看,另一个法术也能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去。有了这些东西和下面的牵制着敌人的灰矮人士兵们做保证,于是他就能一面作壁上观,一面等待时机—— 他等待着,观察着,直到蜘蛛骑兵队长驱动坐骑冲入战场,恰好就位于尼摩下方之处。
握住嘉泽莱德·朝尔辛家族的徽章,依旧隐藏在魔法效果中的尼摩缓缓下降,拔出了他祖传的匕首——一把相当特殊的匕首——他落在蜘蛛上,就在骑兵队长身后几英寸,把匕首架上了他的后颈,就在对方的头盔与肩甲之间那处绝妙的空隙。
骑兵猛地一缩,转过身来。依旧处于隐身状态的尼摩一把揪住他的脖子,把淬毒的匕首抵了上去。
蜘蛛骑兵看不到他,却能听到耳边响起尼摩的低语,“你叫什么名字?香巴拉。”
“你是谁?”战士问,尼摩则浅浅地划了他一刀作为回答。
卓尔闷哼一声,尼摩能感觉到他的身体僵硬起来,开始不住地痉挛与颤抖。
“没错,”尼摩的低语传进慢慢死去的队长的耳朵里,“淬过毒的。相当,相当上乘的毒药,它会让你全身麻痹,封住你的喉咙,抽空你肺里的最后一丝气息,还会让你在窒息的时候不至于大嚷大叫。“
卓尔用微弱的,上气不接下气的声音咆哮道:“我的家族会为我复仇的。”
“你的家族也会完蛋,……队长?”
“维托塞特·香巴拉。”卓尔的回答从麻痹了的喉咙中强挤出来。“香巴拉家族的蜘蛛骑兵队——”
尼摩始终微笑着,他撑着因窒息而垂死的卓尔精灵的躯体,让他在鞍子上骑得笔直。嘉泽莱德·朝尔辛家族的神眷之刃一直等到最后一阵喘息的痉挛从维托塞特·香巴拉队长身上散去,直到他那洋红色的眼睛变得呆滞无神。之后尼摩漂浮起来,躲开突然失去控制的凶猛的作战蜘蛛。
蜘蛛发狂了,它咬向一个又一个灰矮人,接着又猛转向它的一只同类。那只蜘蛛的驭手分神去回护自己被疯狂的蜘蛛攻击的坐骑——这工夫一个灰矮人步兵一斧子砍下了他的脑 袋。
在接下来的十来分钟里,尼摩一个人做掉了八个以上的卓尔,灰矮人们也干掉了三个。其余的家伙终于转身逃跑了,他们沿着隧道穿过外部的包围圈,逃回了魔索布莱城。这些人一无所获,而尼摩的战绩则是四只蜘蛛以及那些卓尔的尸体。
尼摩下令派出更多灰矮人增援这里以守住这块阵地,给蜘蛛们备上鞍鞯,做好出发准备, 接着带着维托塞特·香巴拉队长的尸体回他的指挥所去了。
这些都是战利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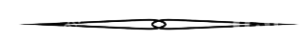
瓦拉斯把水晶举到左眼上,仔细检查着周遭的情况。他正站在隧道边缘沉郁的阴影里, 那隧道其实是一条非常古老的熔岩管,在他所在的位置融入一个金字型洞穴。这个古老的神殿甚至在他没有依靠黑暗视觉的情况下都清晰可见。在瓦拉斯的右边,正对着这个好像是神殿北墙的是一个半径约为七十五尺由石头组成的半圆。弧形的墙壁向上伸长两百尺,直至撑起一个有着还要再高上三十或是四十尺的尖顶的穹顶。两个巨大的窗户嵌在高墙之上,宽度比瓦拉斯的身高多不出多少,却足有八十尺高。一个灵活的小偷得冒着在砖墙上爬上一百尺的风险才能从那儿钻进去。在这些高高的窗户之间,距它们窗台下面几尺的地方有两个又小又黑的孔洞,而且高度足够瓦拉斯不用低头就能钻进去。在这些圆形的孔洞下方又有几个倾斜向下的方形开口,直指向这个废墟黑漆漆的内部。
这些窗户,两个圆形的孔洞,以及方形的开口,让这个废弃了的神殿露出了——明显蓄意地——一副紧皱眉头的神情。
钟乳石从开口的上方边缘垂下,仿佛悬挂的毒牙,几个世纪以来不停地滴下携带矿物质的水,沉淀在圆顶上,形成了一大块白色光滑的补丁,像一顶张扬的歪沿帽盖住了这个大脑瓜顶的另一端。瓦拉斯懒得去想在巨脸形成之前这里举行过什么可怕的仪式。自从他的祖先遗弃了这个地方,好几个世纪已经过去了,时间在这些建筑上留下了无情的印记。但是瓦拉斯知道,包含矿物质的水滴、熔岩以及地震的复仇都没能触及到藏在其中的传送门。之前有两次,瓦拉斯爬进了这个下垂的、忧郁的大嘴,穿过两排雕刻着符文的柱子,跨越两百里抵达撒米尔湖的西北岸,这是条前往辛迪尔林的近路。不过那一切都已经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
瓦拉斯知道他不是唯一一个用过这个传送门的人。
水晶一般都放在他的贴身衬衣里——那件魔法衣物让他有更灵活的脚步和闪电般的反应——和其他许多他在幽暗地域的荒野里戴了一辈子的魔法饰品放在一起。通过水晶,斥候能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大多数被魔法隐藏的人或物,无论那是其天生的能力还是被施加在其身上的法术。
瓦拉斯慢慢地,仔细地检查这张大脸的底部,然后走到被山洞顶部分割成两半的死寂的黑水池的左岸旁。一个在他前面横穿过的斜墙下方有一个洞穴,还有一个更小的——和瓦拉斯来时走的熔岩管相同规模的另一个熔岩管——更高点,在右边。斥候开始仔细的检查神殿废墟的屋顶。这时候,他听到了达妮菲几乎是跺脚一般的脚步声。她正穿过隧道,向他而来。
瓦拉斯没有停止他对这个建筑物缓慢且有条不紊的检查。
他知道不提醒的话达妮菲会从他身边错过;尽管他们的肩膀都快碰到了,她根本看不见他。他已经告诉过达妮菲等在原地,如果她无视他的警告,那么这是她自己的选择。
让她一路跺过去算了。他想。就让她——
当水晶显示出一个只能是栖息在神殿顶部的巨兽爪子的指甲尖时,瓦拉斯浑身的血液都冻结了了。稳住呼吸,达耶特佣兵团的斥候把他的脑袋向后拉了半英寸,放置好水晶,让它仍然紧贴着他的左眼,沿着那个古老面孔的穹顶搜寻。
这个栖息在废墟顶部的生物不太大,至少不像一般的龙那么大,还没瓦拉斯高,翼展大概是它高度的两倍。它舒服而警惕地在穹顶上盘成一团。尽管水晶总是趋向于把呈现图像染红,但是瓦拉斯知道这个怪兽实际上是和他在魔法物品中看到的一样的灰色。即便是透过水晶观察,这生物的轮廓依旧像是巨脸上涂了水彩一样模糊不清。
这就是你隐藏自己的方法。瓦拉斯想着。你和黑暗融为一体。
达妮菲从他身边经过,毫不警惕地大踏步走向熔岩管的大嘴。她站了一会,一只手仔细摸着石头墙,遥望着来时的山洞。瓦拉斯无法提醒她她没有看到巨脸上的龙,但是从水晶里飞快的一瞥,告诉他那条龙已经注意到她了。它慢慢的展开身体,张开了翅膀。
依靠着他长久的训练和丰富的经验,瓦拉斯滑进旁边的岩洞,他可没骄傲到不使用魔法戒指来为自己加速。秘银锁子甲吞掉了他在移动时发出的所有的声音,而且还让他的脚下的步伐安全而无声。把自己隐藏在阴影中,没发出一点和石头刮擦的声响,没反射半丝金属的光晕,瓦拉斯从熔岩管的大嘴沿着斜坡下来,顺着这个巨大空间的碗型边缘来到那张着大嘴的洞穴入口。
他冒着风险瞥了一眼那个生物,在幽暗的洞穴高处也只能大致的描绘出它的轮廓——而且仅仅因为他知道它在那儿。瓦拉斯也同样冒险瞥了达妮菲一两眼,她仍然慢慢地,带着出人意料地优雅向洞穴碗型底部走去。她环视四周,确唯独没有向上看。她的眼睛既没有看到瓦拉斯也没有看到那个像石头一样灰色的龙。
达妮菲慢慢走向池塘的岸边。同时瓦拉斯从他的背上取下短弓,搭箭开弓。
这个女性卓尔除了把自己送进野兽的银餐盘里什么也没做。尽管瓦拉斯渴望看到她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但是他担心昆舍尔;高阶女祭司好像有点喜欢这个莫兰家的战俘,她把她从契德纳萨城的那个女祭司手里抢走时连想都没想。瓦拉斯可不想在任那战俘死掉之后自己费了挺大劲才弄明白,昆舍尔在她俩那场一时兴起的逢场作戏外对她还另有安排。
“瓦拉斯?”女性卓尔向空旷寂静的山洞喊道。
她的声音回荡着。瓦拉斯不禁一凛,同时龙振翅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