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菲利普·阿桑斯
翻译:锅子、塞巴斯汀、姽婳深闺、诺伯、Evenlong、Rainagel
校对:塞巴斯汀、微睡、Evenlong、Rainagel、Pksunking
有什么东西不见了。
赫莉丝卓能觉察到——更确切点说,她感觉不到它了。她感觉不到心灵联结,感觉不到达妮菲了。
通过卓尔密法与一个战俘心灵联结是一种奇特而微妙的体验。它并不是真的每时每刻都能那么鲜明地感应到的。更确切的说这感觉一直都在,隐没于潜意识之中,恰如呼吸与脉搏一般自然。
联结中断的时候她正在跳舞;那些欢迎她加入圈子的女祭司们常常跳舞。他们与特定的女性组成不同的组合,既在神圣之地跳,也在凡俗之所跳;通常是一丝不挂,偶尔也衣着整齐;有时全副武装着铠甲与武器,有时带着祭司用的艺术品或水果;在篝火边轻旋,在雪地里劲舞;他们在夜色中跳——赫丽斯特依旧觉得还是晚上比较自在——也在白昼里跳。她还在学习每个不同的舞蹈地点所代表的意义,组合中的微妙的变化与步法,节奏与动作。
当那感觉袭来的时候,赫莉丝卓不由得停下了舞步。其他女祭司都没注意到她,没人停下舞步,欢快的祭典还在继续。
赫莉丝卓跌跌撞撞地从舞圈里出来,厄运将至的预感驱使她向与瑞厄德分手的地方急奔而去。她知道武技教官因为没被女祭司的圈子所接纳而烦躁得很。赫莉丝卓一走就是几个钟头,但当她归来后依旧有很多问题无从释疑。她没办法确认瑞厄德是否爱她—— 她甚至还无法完全确定什么是“爱”,她自己还在继续学习,而战士却止步不前。但他陪着她继续留在这片饱受阳光蹂躏的寒冷森林中,周围全是那个(在他看来依旧是个叛逆者)女神的信徒们。
她跌跌撞撞地冲进他们俩住的那间寒冷黑暗的小屋,打断了他正在进行的沉冥训练。他正双眼紧闭地倒立着,双腿向后弯折,脚尖绷得笔直。武技教官有时会一连几个钟头保持这个姿势,换赫莉丝卓来做,撑不过一两秒。
她刚一进门,武技教官就睁开了睛。想必是从她的表情中看出了什么端倪,他干净利落地向前一跃而起,没有半点晕眩或是混乱之态。
“赫莉丝卓,”他问,“出什么事了?”
她张开嘴想要作答,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一定出事了。”他四下打量着房间。
“瑞厄德,我……”见他开始着装,她连忙开口。
他先是一把抓起分裂者——他那把巨大的双手剑——接着飞快的把他入鞘的短剑装到武装带上去。当他拿起铠甲的时候她按住了他的手臂。他的皮肤摸起来很温暖,几乎是干热的。那深黑的皮肤紧紧包裹着结实的肌肉,就仿佛是岩石雕琢而成的一般。
“不,”她终于从蛛网般纷乱的思绪中回过神来,“放下它。”
他停下来看着她,等待着。她能从他的目光里看出焦躁来,混杂着挫败的焦躁。
“怎么回事?”他问,她能看出来,他刚一开口就明白了。
她笑了,而他叹了口气。
“达妮菲。”她终于开口。“我再也感觉不到她了。心灵联结被破坏了。”
他瞪大了眼睛,她能察觉到他的惊讶。没必要感到惊讶,这只是心灵联结被破坏了,但他看上去期待听到别的什么消息。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他问,把铠甲靠在床旁的墙边。赫莉丝卓摇了摇头。
“她死了?”他不露声色地问。
“恩。”赫莉丝卓答道,“也许吧。”
“这怎么会让你如此惊慌失措?”
赫莉丝卓向后退去——尽管这问题问得合情合理,她还是被狠狠地震了一下。
“这怎么会让我惊慌失措?”她重复道。“这是因为……我在担心,她自由了。我不再是她的主人,她也不再是我的战俘。”
瑞厄德皱起了眉头,耸肩道,“这对你来说算是问题吗?”
她张口打算回答,却又一次无言以对。
“我的意思是说,”武技教官继续说下去,“我不认为你的新朋友们会赞成这种关系, 不是吗?难道那些叛——我是说,这些异教的女祭司也有战俘吗?“
她笑了,他走到一旁,装作专心致志于把分裂者放回到他们床下的恰当的位置去。
“她们不是叛徒女祭司,瑞厄德,”她说。
他简单地点了点头作为回应,接着坐到床边去,看着她。
“不,她们就是。”他的声音同他的目光一样沮丧而挫败。“她们也背叛了她们的种族, 就跟我们俩一样千真万确。现在我一直在问我自己,成为一个叛徒就那么大逆不道吗?”
赫莉丝卓走过去他脚边,跪坐了下去,双手覆上了他的膝盖。他抚摩着她面颊旁那长长的白发——那动作仿佛是出于直觉。
“不。”即使在小屋的一片寂静中,她的声音也几不可闻。“并没有那么糟。事实上所谓叛徒也只是对于我们自己而言,而我觉得我们最后会坦诚以对我们自己……还有我们彼 此……”
当看到他脸上的表情时,赫莉丝卓的心猛地往下一沉。他不相信她所说的这些话,而她偏偏忍不住期待着他应该相信。
“那是什么样的感觉?“他问。她摇了摇头,没明白他的意思。“感觉不到心灵联结。”他说。
她移换了重心,坐到了地板上,头靠着他那强健结实的大腿。
“我能感觉到我过去生命中的一切都正在一点点被新的东西所取代。” 他的手指轻轻描绘着她肩膀的轮廓,这触碰让她战栗起来。
“伊莉丝翠取代了罗丝,”她说,“光明取代了黑暗,包容取代了猜疑,爱取代了恨。” 一种陌生的温暖而湿润的感觉充斥在她的双眼中,她泪流满面。
“你还好吧?”他关切地低声问道。赫莉丝卓擦去眼泪,点了点头。
“恨,”她重复道,“被爱所取代了,那么显然自由也就取代了奴役。”
“死亡也取代了生存?”瑞厄德问。
赫莉丝卓叹了口气。
“也许吧,”她说,“但不管怎样,她都自由了。她的灵魂去了死后的世界,我只希望等待她的不要是那空旷荒芜的深坑魔网。说不定她还在幽暗地域,健康、自由地活着。不管是死是活,她都同样得到了自由。”
“自由……”瑞厄德重复道,就好象他以前从不曾说出过这个词,需得一遍遍练习。
他们就这样坐了很久,直到赫莉丝卓的腿都麻了。察觉到她的不适,瑞厄德一把把她抱到床上来紧挨着自己,动作就好象她没有重量似的。他拥她入怀,仿佛卫护着珍珠的贝壳。
“我们得回去,”她低语道。他拥紧了她。
“不是你想的那样,”她轻声说,她知道他想回去幽暗地域,再不回头。“是时候去找昆舍尔和她的探险队了。”
“截住他们?”他问,话语伴着灼热的气息摩挲着她的颈项。
“不。”
“跟着他们?”他紧贴着她的发丝道,手扣紧了她的腰肢。
赫莉丝卓紧紧,紧紧地抱住了战士,直到她觉得自己已经整个贴在战士身上,融进了战士那暗夜般深黑的皮肤中去。
“对,”她说,“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他们都得带上我们,他们将把我们带到罗丝那里去,而我们就能了结这一切。”
赫莉丝卓没有拒绝他接下来进一步的温存,这件事他不愿再去想,而她也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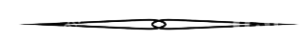
身在混沌之舟的费瑞恩凭栏而立,听任目光深陷在阴影湖虚无的黑暗中,因为除此之外他实在想不出别的事好做。去采办补给的瓦拉斯和达妮菲还没回来,他用大批的恶魔把船喂得饱饱的,鼠魔船长一声不吭的蜷在一旁,而阿丽扎也全然不见踪影。
奥术学院导师在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审思之前的对话,得出的仍旧是原来的结论:爱璐魔女没告诉他一点有用的讯息,但也没从他嘴里套出一个字。可她确实找到了自己,也见到了这艘船。她知道他们要去哪里,要去做什么。但话又说回来,但凡亲历过契德纳萨城陷落的人用膝盖都能想出来他们的目的。
他将爱璐魔女的身影从脑海中抹去,凝神望向黑暗的更深邃处,但仍是一无所获。费瑞恩不用转身就知道昆舍尔背抵扶栏坐着,心不在焉地通过心灵感应与受困于蛇首鞭中的小魔鬼闲聊,后者赋予这件武器邪祟的智能。他根本想象不出跟一个被塞进鞭子蛇头的恶魔会有什么好说。
反正不论他们在谈什么,对昆舍尔似乎都没什么帮助。就费瑞恩看来,这个高阶女祭司就是在安静的发疯。她的确总是显得阴郁、喜怒无常,但最近她开始变得……焦躁不安。
她的半恶魔外甥越是无聊就越发暴躁易怒。杰格拉德把他浓烈的憎恨通过视线投注于鼠魔身上;而拉尔萨布只当他压根就不存在。
费瑞恩眼角的余光瞄到有什么在动,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腾地从扶栏旁撤开,此时一只浑身湿漉漉的瘦老鼠顺着骨节和软骨构成的栏杆,从他面前狼狈蹿开。
费瑞恩看着它跑掉,心不在焉地想它要往哪跑。反正是什么干的地方,他想。
背后闹哄哄地,是杰格拉德在瞎折腾。
费瑞恩重新靠回扶手,正要再望向远处那难以看透的重重暗幕,又有一只老鼠急匆匆跑过他面前。
“见鬼。”奥术学院导师轻声自言自语。
他掉过头想不咸不淡地向杰格拉德抱怨几句,但他的话卡在了喉咙里。
经过他身边的远不止两只老鼠。它们足有数十只,甚至上百只;它们像潮水般席卷过杰格拉德的身躯。
不太对劲。费瑞恩心想,同时诧异的感到在这沉闷的破船里呆了这么长时间,自己的脑袋竟然变得那么迟钝。
魔裔卓尔看上去烦透了。老鼠们爬在他身上,缠住他的头发,啃咬他所有暴露在外的肌肤。但他们咬不穿半恶魔坚硬的皮肤。更多老鼠爬上了甲板。费瑞恩听到船的另一边传来水花四溅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数十只,甚至数百只更多的老鼠正游上这艘恶魔之船。
费瑞恩着手给自己施展防御法术,同时看到昆舍尔终于抬起头,望向她的外甥。
蜘蛛教院的女教长眼睛睁大开来,但随即又皱紧,她看到杰格拉德用自己较大的那双拳头一只只地锤扁老鼠,而用较小的那对手掌把耗子从脸上弄掉。昆舍尔慢慢站起来,她的蛇鞭松松垮垮的垂下来,亲昵地环住她的双腿。
“杰格拉德?”她问。
“耗子。”魔裔卓尔恼怒的嘟哝着。
昆舍尔走向魔裔卓尔的工夫,费瑞恩又往自己身上加了更多的魔法防护。
“拉尔萨布。”费瑞恩用冷酷而强硬的声音说。
鼠魔听到自己的名字打了个激灵,没敢抬头看。
“拉尔萨布,你在做什么?”费瑞恩在两个防护法术的施展间隙问道。“让它们停下, 马上。”
鼠魔用压抑着怒火的目光盯着他,嘶嘶道:“不是我干的,那不是我的老鼠。”
费瑞恩难以撼动内心的直觉:鼠魔船长说的是实话,至少从某种角度来说算是实话。
“费瑞恩?”法师觉察出昆舍尔的声音中泄漏出一丝—不,不止一丝的惶恐。“这些老鼠是怎么回……”
“你们都当心点。”费瑞恩说,同时开始准备一个更具攻击性的法术。“那有另一个……”
一团黑暗吞没了昆舍尔。
任何卓尔都能做到这一点,但并非只有卓尔才能这么做。
从缓缓涌动的黑暗之云中回荡着毫无疑问的搏斗声。有什么东西撞倒在甲板上,还有某物碎裂的的声音。
费瑞恩在施放出原定法术之前就调转了方向,转而施放另一个法术以期消除魔法黑暗。费瑞恩只听得结界内铮然作响,却不知那是金铁相击之音还是骨骼迸裂之声。
他放出了法术,黑幕随即散去。
众目睽睽之下,昆舍尔正趴在骸骨雕琢的甲板上摸索自己的蛇首鞭,那玩意却正好在她够不到的地方。她的鼻子鲜血直流,每挺一下背都疼得五官纠结。
在她身前立着另一只鼠魔。
这只恶魔酷似拉尔萨布,也是直立行走。不过体型小些,也来得纤弱些;它褴褛的衣物几乎将长满斑杂灰毛的身体一览无遗的暴露出来,长长的粉色尾巴脓包密布,无情的黑眼杀机恶陈,俯视着脚下的高阶女祭司。一口唾沫星黏在它利齿勾连的嘴角,躁动的黄疸色双爪从骨节暴突的长手指尖弯出自然的弧度。
“杰格拉德……”费瑞恩向后瞥了一眼魔裔卓尔。
半恶魔卓尔从头到脚的每一寸都被老鼠占得满满。似乎暗湖所有的害兽们正在魔裔卓尔的全身举办家族联欢。虽说他一次能料理四只,但它们涌来的速度仍超过他屠杀的速度。费瑞恩凭借相关法术快跑起来,往昆舍尔的方向迈出了几步。
鼠魔用尾巴在她背上狠砸了一记;高阶女祭司的脸咚地砸上骨制甲板。伴着溅出的寥寥血星,女祭司闷哼一声,忍下这一击。
费瑞恩在心中赞许。但一个念头令他打消了首选法术。太多了,他想道,在这一个敌人身上用的太多了……
奥术学院导师转头望向拉尔萨布,恶魔船长的视线正飞快地在昆舍尔与另一只鼠魔间切换。
他在试探我们。费瑞恩想。这狡猾的杂种唤来了一个同族攻击我们,令我们不得不泄露自己的力量和弱点。
拉尔萨布可能是被绑上了,但它毕竟是恶魔;它们永远不会停止算计,总能找到脱身的方法。
那第二只鼠魔一爪挠过昆舍尔的双腿,撕开深深的伤口,她立刻回踹它。恶魔跳到她踢不到的地方;高阶女祭司回手去取鞭子,可她仍然够不到。毒蛇们看起来吓坏了,无法统一动作移向她。
费瑞恩迅速吟诵出一段韵律,右手同时飞速结印。在魔法的推动下,甲板上的鞭子向前滑出几寸,正好到了昆舍尔手边。
在高阶女祭司的手指摸上蛇首鞭的瞬间,费瑞恩无声地笑了:刚刚的施术不过是一个戏法,随便哪个奥术学院的一年级生都能掌握这个简单的变化。关于自己力量的界限,拉尔萨布甭想看出一点门道。
鼠魔冲着昆舍尔嘶嘶直叫,退得更远了;它的尾巴在身后扭动着,双爪蠢蠢欲动。显然这恶魔以为它离开了鞭子的攻击范围——它错了。
昆舍尔鞭子上的五只鞭蛇足有五尺长,这使得此件兵器的威胁距离相当远。牙关紧咬, 双目燃烧着狂野的激怒,仍倒在甲板上的高阶女祭司等不及站起来就运起鞭子。她一甩出, 五只鞭蛇便竭尽所能得向前伸长。鼠魔畏缩了一下,但似乎仍然认为那武器打不着它。鞭蛇再度用力向前冲去,越伸越长,越拽越细,活生生比原本射程又拉长了几尺。
没来及完全弄清楚状况的鼠魔仍足够敏捷的避开了卷来的长鞭。只有一只鞭蛇成功将它锋利的尖牙扎入了鼠魔的身体。随着鞭子抽回,鼠魔的硬皮上被尖牙挖出一道道长长的血痕。
恶魔失声尖叫,又尖又利,弄得费瑞恩耳中嗡嗡直响。
换成别的生物估计早就死掉了;每只蛇分泌的毒液都是致命的。费瑞恩从未想象过昆舍尔这般激烈作战的狂暴样子,更别提亲眼见过了。她绝不会让鞭蛇们嘴下留情。那些毒液应该足以放翻洛斯兽。
但中了鞭首蛇毒的恶魔也不是任人鱼肉的家伙;它是鼠魔,而费瑞恩在长期研究恶魔的习性后早已得知它们共同的特性——毒素对它们没有实际效力。鞭子曾经伤过船长,却没有要它的命。费瑞恩明白它能承受的远不止这些。即使是一只像鼠魔一样相对弱小的恶魔,或者像眼前这只不可算作族群中的出类拔萃者,也往往能承受极端的寒冷与高温,并且运用天生的魔法能力——比如刚才的那记黑暗术——打昆舍尔一个措手不及。鼠魔能够召唤它们的耗子同宗,正如缠住杰格拉德的那一群。费瑞恩觉得自己记得关于鼠魔啮咬的信息,不过当前他难以回忆起来。当然,同其他的塔纳厘如出一辙,闪电攻击仅仅是给他们瘙痒。
哪怕是在上述念头飞闪而过的瞬间,费瑞恩的手也已搭上了能放出闪电束的魔杖。意识到这样只是徒劳,奥术学院导师转而取下一寸之外的另一根。
费瑞恩犹豫了一下,看着昆舍尔灵巧地单脚跃起,面对鼠魔。恶魔冲她嘶叫,可昆舍尔视若无睹。高阶女祭司再度噼啪作响的朝鼠魔甩动鞭子,这次有三只鞭蛇深深咬住了鼠魔的胸膛。那东西朝毒蛇挥出自己剃刀般锋利的爪子,不过蛇身及时缩回,让双爪扑了空。
无视失手的鼠魔旋身冲卓尔女祭司抡出沉重的长尾巴。这一下打得结实,昆舍尔抬起左手,用手臂上的小圆盾挡住攻击。费瑞恩本以为她的胳膊骨折定了,但她出人意料的挡开了尾巴。
然而,鼠魔比昆舍尔收招要快,它的尾巴随即反抽回来,角度放的更低,啪地击中了女祭司的侧肋。
费瑞恩听得她倒抽一口凉气。昆舍尔几乎是跌跌撞撞的往旁边踉跄了几步。恶魔挂着一脸险恶的笑容逼近,意图在咬住她的同时用爪子刺穿她。
费瑞恩吸了口气,准备在恶魔刚要发动攻击时就念出启动魔杖的命令,它迎面撞上了昆舍尔的圆盾。随着“咣”的一声闷响,鼠魔撞了个鼻血肆流。恶魔的爪子徒劳地在昆舍尔面前挥动着,而五只鞭蛇咬准了敌人身上最脆弱的部位,狠狠刺入毒牙。剧痛让鼠魔哀嚎不已。
嗬,费瑞恩想,没急着激活手里的魔杖——看起来她进入状态了。
费瑞恩的视线转向了拉尔萨布,停了下来。被缚的鼠魔正瞧着他,打量着那根魔杖,期待的神色在恶魔船长脸上显露无疑。
费瑞恩看看手上的魔杖,又看看拉尔萨布。他们目光相交,拉尔萨布对他一笑。
费瑞恩报以一笑,将魔杖推回腰间。拉尔萨布很好地掩饰了自己的沮丧,转而继续观看昆舍尔与他同族的战斗。
费瑞恩决定帮杰格拉德一把。拉尔萨布会领教到魔裔卓尔的能耐,如果费瑞恩能解决掉成波的老鼠,让杰格拉德得以援助昆舍尔,那另一只到处蹦跶的鼠魔眨眼就能被干掉,费瑞恩也就不需要再出什么力来显山露水了。
就在费瑞恩打定主意之时,一连串噼噼啪啪的响声又将他的注意力引到昆舍尔身上。蜘蛛教院院长掰开一整节的扶栏,船上的软骨和骨节像干蘑菇柄一样断裂,凋落下来。昆舍尔将鞭子收在腰带,撞塌鼻子的鼠魔滴淌着鲜血在她跟前晃蹒跚着。她高举起那根十尺长的扶栏。
费瑞恩迅速开始准备救助杰格拉德的法术;昆舍尔也发动攻势。高阶女祭司飞快将栏杆用力砸向鼠魔。还没有被鼻血完全糊住双眼的恶魔狼狈往后退避,抢在最后一刻及时跳开。栏杆砸在甲板上,瞬时崩裂,骨片四下弹飞,有几块还弹到了费瑞恩的魔法护盾和结界上, 他还看见几片碎骨扎到了围攻杰格拉德的两只老鼠。
昆舍尔在近乎疯狂的震怒中咆哮着,费瑞恩感到不安,这样子并不符合她蜘蛛教院女教长的身份。
甲板上被扶栏砸到的地方血泊滩滩,这是混沌之舟流的血。法师不确定自己能否修好它, 任何更进一步的伤害都可能拖延甚至中止他们的旅程。然而,费瑞恩也不想大声提醒什么; 所以如果昆舍尔不看他,他也没法打手势告诉她别再拆船了。
费瑞恩对着杰格拉德身上的鼠群施展了法术,它只是是个简单戏法,编织出一道闪烁而多彩的圆锥形力场能量。费瑞恩谨慎地挑选好作用位置,以确保法术效果能恰好地顺着魔裔卓尔遍布老鼠的身躯扫下来。法术一点都没伤着杰格拉德,但从他身上扫下了相当多的老鼠。它们跌在甲板上,毛茸茸的潮湿躯体翻滚、抽搐着。
杰格拉德狂叫着摆动全身,从他厚密的雪白头发把老鼠、血液和水滴甩得满甲板都是。魔裔卓尔又解决掉五只老鼠,两手各捏死一只,踩死三只。
费瑞恩抽空瞥了拉尔萨布一眼,看到鼠魔一脸挫败的失望。刚才那又是一个奥术学院教授的简单法术,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学会了,拉尔萨布明显识别出了这一点。
费瑞恩重新转向杰格拉德并叫道:“别管老鼠了,杰格拉德。你的主子正被恶魔缠着呢。”
杰格拉德再吼一声,往鼠魔船长脚边丢下更多或死或昏的老鼠,一步跃到鼠魔船长身边举起四条胳膊,准备把它撕成碎片。拉尔萨布一退再退,握紧拳头死命地撑动绳结。
“别!”昆舍尔喝道,她的叫声沙哑而疯狂。“不是那一只,见鬼!干掉这只!”
杰格拉德飞快的转过身,他的眼中倏地闪过昆舍尔与另一只鼠魔正在对战的景象。
第二只鼠魔充分利用了昆舍尔一瞬间的分心,突破了她的防守。它用爪子深深划过她的腹部,割开盔甲,鲜血横流。昆舍尔因剧痛面容扭曲,牙关紧咬,但随即狠狠的还以颜色。两人都踉跄了一下,岌岌可危地各自站在一堆碎掉的骸骨栏杆和船受伤流出的鲜血里。
杰格拉德扬起嘴唇,露出一排残忍锋利的獠牙。随即魔裔卓尔加入了混战。